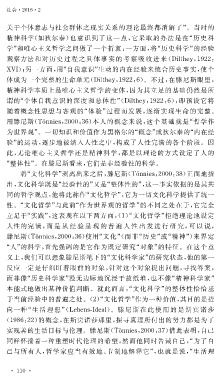Page 117 - 《社会》2016年第2期
P. 117
社会· 2016 · 2
关于个体意志与社会群体之现实关系的理论最终都消解了”。当时的
精神科学(如狄尔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采取的办法是在“历史科
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之间做了一个折衷:一方面,将“历史科学”的经验
,
观察方法和对 历 史 过 程 之 具体 事实 的 考 察 吸 收 进 来 ( 犇犻犾狋犺犲 狔 1922 :
犡犞犐 );另一方面,用“自我意识”生动的内在经验来统合历史事实,使个
,
体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单元( 犇犻犾狋犺犲 狔1922 : 6 )。不过,在滕尼斯眼里,
精神科学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变体,因为其立足的基础仍然是所
谓的“个体自我意识的深度和总体性”( 犇犻犾狋犺犲 狔1922 : 6 ),即预设它将
,
随着概念性思想与客观的“体验”过程而发展,逐渐实现生命的完整。
用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2000 : 36 )本人的概念来说,这个基础就是“哲学作
为世界观”。一切知识和价值作为黑格尔的“概念”或狄尔泰的“内在经
验”的运动,逐步地被纳入人性之中,构成了人性完满的各个阶段。因
此,无论唯心主义哲学还是精神科学,都是以理论的方式设定了人的
“整体性”。在滕尼斯看来,它们是非经验性的科学。
将“文化科学”剥离出来之后,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2000 : 38 )正面地指
出,文化科学既是“经验性的”又是“整体性的”,这一事实依据的是其共
同的哲学观点,他将此称作“文化哲学”,它为一切文化科学提供了统一
性。“文化哲学”与此前“作为世界观的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
立足于“实践”,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 )“文化哲学”拒绝理论地设定
人性的完 满,而 是 从 经 验 呈 现 的 普 遍 人 性 出 发 进 行 研 究,可 以 说,
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2000 : 36 )使用“文化”(而非“历史”或“精神”)来界定
“人”的科学,首先强调的是它作为既定研究“对象”的特征。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可以想象滕尼斯笔下的“文化科学家”的研究状态,他的第一
反应一定是仔细盯着眼前的对象,针对这个对象提出问题,寻找答案,
而非像“历史科学家”漫无边际地沉浸于故纸堆,也不像“精神科学家”
本能式地做出某种价值判断。就此而言,“文化科学”的整体性恰恰基
于当前经验中的普遍之处。( 2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价值,其目的是指
向一种 “生 活 理 想”( 犔犲犫犲狀狊犐犱犲犪犾 )。滕 尼 斯 在 此 使 用 的 是 斯 宾 诺 莎
( 1986 : 22 )的概念,在斯宾诺莎那里,探寻真理所付出的努力都是为了
实现善的生活目标与伦理。滕尼斯( 犜狀狀犻犲狊 , 2000 : 37 )借此表明,自己
同样怀揣着一种重塑时代伦理的希望,然而他同时告诫自己,“为了自
己与所有人,哲学家应当有效地、节制地解释它”,也就是说,“生活理
· 1 1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