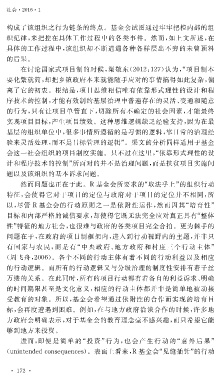Page 180 - 《社会》2016年第1期
P. 180
社会· 2016 · 1
构成了该组织之行为链条的终点。基金会试图通过牢牢把控内部的组
织纪律,来把控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的各类事件。然而,如上文所述,在
具体的工作过程中,该组织却不断遭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未曾预料
的后果。
在讨论国家式项目制的时候,渠敬东( 2012 : 127 )认为,“项目制本
要化繁就简,却把乡镇政府本来就能随手应对的事情搞得如此复杂,偏
离了它的初衷。根结是,项目思维相信唯有依靠形式理性的设计和程
序技术的控制,才能有效制约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灵活、变通和随意
的行为,只有让项目单管直下,切除所有不确定的社会因素,才能最终
实现项目目标,产生项目绩效。这种思维逻辑缺乏经验支持,因为在最
基层的组织单位中,很多事情所遵循的是习惯的逻辑,靠日常的治理经
验来灵活处理,而不是目标管理的逻辑”。渠文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基金
会这一社会组织的项目制度实施。只不过在这里,“依靠形式理性的设
计和程序技术的控制”所面对的并不是治理问题,而是扶贫项目实施问
题以及该组织的基本诉求问题。
然而问题也正在于此。 犚 基金会所要求的“取法乎上”的组织行动
特征,会使得它对于项目的定位与政府对于项目的定位并不相同,所
以,尽管 犚 基金会的行动原则之一是依附性运作,然而因其“培育性”
目标和内部严格的诚信要求,却使得它既无法完全应对真正具有“整体
性”特征的地方社会,也很难与政府的各类项目完全合拍。更为棘手的
问题在于,在政府的项目制框架内,进入到行动视野内的主题,并非只
有国 家 与 农 民,而 是 有 “中 央 政 府、地 方 政 府 和 村 庄 三 个 行 动 主 体”
( 周飞舟, 2006 )。各个不同的行动主体有着不同的行动利益以及相应
的行动逻辑。而所有的行动逻辑又与分级治理的制度性安排有着千丝
万缕的关系。在此同时,所有的项目行动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明确
的时间期限甚至是文化意义,相应的行动主体都并非是简单地被动接
受教育的对象。所以,基金会希望通过依附性的合作而实现的培育目
标,会再度遭遇到困难。例如,在与地方政府洽谈合作的时候,许多地
方政府会明确表示,对于基金会的教育理念毫不感兴趣,而只希望它能
够到地方来投资。
进而,即便 是 简 单 的 “投 资”行 为,也 会 产 生 行 动 的 “意 外 后 果”
( 狌狀犻狀狋犲狀犱犲犱犮狅狀狊犲 狇 狌犲狀犮犲狊 )。表面上看来, 犚 基金会“见缝插针”的行动
· 1 7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