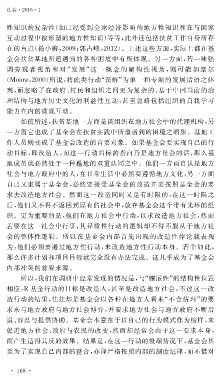Page 176 - 《社会》2016年第1期
P. 176
社会· 2016 · 1
性知识的复杂性(如已经受到全球经济影响的地方性知识和在与国家
互动过程中被形塑的地方性知识)等等;此外还包括扶贫工作自身所存
在的盲点(杨小柳, 2009 ;郭占峰, 2012 )。上述这些方面,实际上都在基
金会扶贫基地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中有所体现。另一方面,若一味强
调 旁 观 者 视 角 和 对 “发 展”这 一 概 念 的 解 构 性 视 角,则 可 能 如 摩 尔
( 犕狅狅狉犲 , 2000 )所说:将此类行动“误解”为单一和专制的发展话语之体
现,而忽略了在政府、村民和组织之间更为复杂的、基于中国当前的治
理结构与地方历史文化的利益性互动,甚至忽略包括组织的自我学习
能力在内的微观互动。
如前所述,扶贫基地一方面是该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代理机构,另
一方面它也成了基金会在扶贫实践中所遭遇到的困境之缩影。基地工
作人员则变成了基金会改造的首要对象。如果基金会要实现自己的行
动目标,即改造人,而这一行动目标的指向乃是地方社会的话,那么基
地成员就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双重认同之中。他们一方面自认是地方
社会与地方政府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必然要遵循地方文化,另一方面
自己又隶属于基金会,必然要接受基金会的改造并要按照基金会的要
求去改造地方社会。然而这一改造同时又是有时限的,在这一时限之
后,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到原有的社会中,放弃基金会这个带有光环的组
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地方社会中行动,以求改造地方社会,然而
若要在这一社会中行事,其异质性行动的逻辑却不得不服从于地方社
会的整体性逻辑。所以在基金会内部首先出现的改造性悖论就表现
为:他们必须要通过地方性行动,来改造地方性行动本身。若非如此,
那么许多计划和项目目标就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这几乎成为了基金会
内部冲突的首要来源。
所以,我们在调研中经常发现的情况是,与“镶嵌性”的结构性位置
相应, 犚 基金行动的目标是改造人,甚至是改造地方社会,不过这一改
造行动的结果,往往却是基金会以各种在地方人看来“不合情理”的要
求来与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博弈,并要求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不断后
退、容忍与提供协助。基金会本意在于以自己的行为模式作为榜样,来
促进地方社会、政府与农民的改变,然而却经常会由于这一要求本身,
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结果是,在这一行动的极端情况下,基金会甚
至为了实现自己内部的整合,亦即严格按照内部的制度纪律,而不惜对
· 1 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