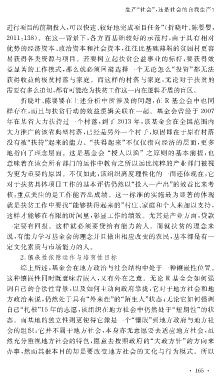Page 173 - 《社会》2016年第1期
P. 173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
进行项目的前期投入,可以快速、较好地完成项目任务”(折晓叶、陈婴婴,
2011 : 138 )。在这一背景下,各方面基础较好的示范村,由于具有相对
优势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往往比基础薄弱的贫困村更容
易获得各类资源与项目。若要树立起扶贫公益事业的标杆,要获得效
益显著的工作模式,那么就必须回避选择一个无论怎么“投资”都无法
获得收益的极贫村落与家庭。而这样的村落与家庭,无论对于扶贫的
需要有多么迫切,都有可能沦为扶贫工作这一内在逻辑矛盾的盲区。
折晓叶、陈婴婴在上述分析中所涉及的问题,在 犚 基金会中也同
样存在,而且与扶贫行动的效益逻辑关联在一起。基金会曾经于 2007
年在某省大力扶持过一个村落,到了 2013 年,该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
大力推广的该省典型村落,已经是另外一个村子,原因即在于原有村落
没有被“扶持”起来的能力。“扶得起来”不仅仅指向经济的层面,更多
地指向了理念层面。这是基金会 “授人以渔”之原则的基本前提,也
意味着在该会所有部门的运作中教育之所以远比纯粹的产业部门被视
为更为重要的原因。不仅如此,该组织高度理性化的一面还体现在,它
对于扶贫具体项目工作的基本评估仍然以“投入—产出”的效益比来考
核:重点关注的是工作能否出成绩。这一标准的实施最为显著的体现
就是扶贫工作中要找“能够扶得起来的”村庄、家庭和个人来加以支持,
这样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彰显工作的绩效。尤其是产业方面,贷款
一定要有回报。这样就必须要贷给有能力的人。而就扶贫的理念来
说,有能力学习基金会的理念并且做出相应改变的农民,基本都是有一
定文化素质与市场能力的人。
2. 镶嵌性依附运作与培育性目标
综上所述,基金会在地方政治与社会结构中处于一种镶嵌性位置。
这种镶嵌性同时既意味着嵌入,又有外在之意。无论 犚 基金会如何强
调自己的合法性背景,以及如何主动向政府靠拢,它对于地方社会和地
方政治来说,仍然处于具有“外来性”的“陌生人”状态;无论它如何强调
自己“扎根” 15 年的志愿,该组织在地方社会中仍然处于“短期性”的状
态。而基地的独立性则更使得它像是一个“镶嵌”到地方政府与地方社
会的组织:它并不属于地方社会,本身亦无意愿要去适应地方社会,虽
然充分重视地方社会的特色,愿意去按照政府的“大政方针”的方向来
办事,然而其根本目的却是要改变地方社会的文化与行为模式。所以
· 1 6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