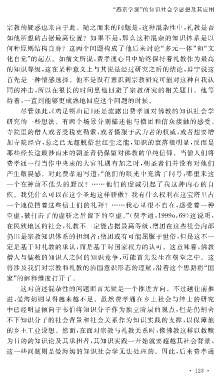Page 130 - 《社会》2015年第4期
P. 130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宗教的疑惑也来自于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混杂性中,礼教是否
如他所想的占据最高位置?如果不是,那么这种混杂的知识体系是以
何种原则结构自身?这两个问题构成了他后来讨论“多元一体”和“文
化自觉”的起点。如前文所说,费孝通心目中始终保持着礼教作为最高
的知识等级,这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经过研究之后的结论,毋宁说这
首先是一种情感选择。他不是没有意识到宗教研究可能对这种自我认
同的冲击,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回避了宗教研究的相关题目。他等
待着,一直到能够更成熟地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
尽管如此,《鸡足朝山记》还是流露出费孝通对佛教的知识社会学
研究的一些想法。有两个场景分别描述他与僧团和信众接触的感受。
寺院里的僧人或者受税吏勒索,或者慑服于武力者的权威,或者想要增
加寺院经营,总之已无超脱俗世红尘之能,知识的衰落很明显,反而是
那些经长途跋涉而来的朝圣者仍保留对佛教的单纯信仰。当僧人们将
费孝通一行当作中央来的大官礼遇有加之时,朝圣者们并没有对他们
产生敬畏感。对此费孝通写道:“他们的眼光中充满了问号:哪里来这
一个在神前不低头的野汉?……他们的虔诚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自
疚。我凭什么可以在这个圣地这样骄傲?我有什么权利在这宝塔里占
一个地位挡着这些信士们的礼拜?……我心里很不自在,感受着一种
空虚,被打击了的虚骄之后留下的空虚。”(费孝通, 1999狅 : 69 )这说明,
在民族地区的社会,礼教不一定能占据最高等级,僧团在这些社会内部
仍旧是宗教知识体系的担纲者;僧团或有可能屈服于世俗,但是这不一
定是基于对礼教的承认,而是基于对国家权力的认可。这意味着,佛教
僧人与儒教的知识人之间的知识竞争,可能首先发生在朝堂之中。这
将涉及我们对宗教和礼教的治国意识形态的理解,沿着这个思路将“国
家”的解释维度打开了。
这对前述混杂性的问题而言无疑是一个推进方向。不过越往前推
进,曼海姆则显得越来越不足。虽然费孝通在乡土社会与绅士的研究
中已经明显倾向于韦伯将知识分子作为独立阶层的观点,但是仍割舍
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作为知识实践的支撑,以保障他
的乡土工业设想。然而,在面对宗教与礼教关系时,像佛教这样以救赎
为目的的知识论及其承担者,其知识实践一开始就要超越其社会背景,
这一些问题则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无法处理的。因此,后来费孝通
·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