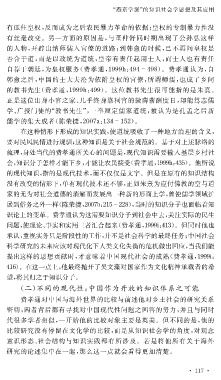Page 124 - 《社会》2015年第4期
P. 124
“燕京学派”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
有压住皇权,反而成为之后农民暴力革命的依据;皇权的专制暴力性没
有丝毫改变。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与董仲舒同时期出现了公孙弘这样
的人物,开辟出纳师儒入官僚的道路;到韩愈的时候,已不再问皇权是
否合于道,而是以政统为道统,皇帝有责任起用士人,而士人也有责任
自荐于朝廷,为皇权服务(费孝通, 1999犺 : 494-498 )。费孝通认为,自
韩愈之后,中国的士大夫沦为依附皇权的官僚,所谓师儒,也成了乡间
的教书先生(费孝通, 1999犺 : 499 )。这位教书先生很可能指的是朱熹。
正是这位出身小官之家、几乎终身靠祠官的微薄薪酬度日,却能笃志儒
学、广授门徒的“教书先生”,一举厘定儒家道统,被认为是孔孟之后新
儒学的集大成者(陈荣捷, 2007犪 : 134-152 )。
在这种情形下形成的知识实践,使道统吸收了一种地方治理的含义,
要对民风民情进行规驯;这种知识是关于社会规范的。基于对上述脉络的
梳理,身处当代的费孝通所关心的问题是,现代知识需要输入基层乡村社
会,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下乡,才能让农民接受(费孝通, 1999犺 : 435 )。他所说
的现代知识,指的是现代技术,而不仅仅是文字。但是在原有的知识结构
没有改变的情形下,单有现代技术还不够,正如朱熹为应付佛教的空与道
家的无为对社会道德的消解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曾使儒学领域扩
展到俗务之外一样(陈荣捷, 2007犫 : 215-228 ),当时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知
识论上的变革。费孝通认为这需要知识分子到社会中去,关注实际的民生
问题,使理论、事实和实用三者汇合起来(费孝通, 1999犻 : 413 )。但同时他也
承认,重视实务只是阶段性的工作,并不是社会科学的最终任务;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的未来应该对现代化下人类文化失衡的危机做出回应,当我们能
提出这样的思想贡献时,才意味着中国现代社会的成熟(费孝通, 1999犻 :
416 )。在这一点上,他最终抛开了吴文藻对国家作为文化精神承载者的希
望,将其归之于知识分子。
(二)不同的现代性:中国作为开放的知识体系之可能
费孝通对中国与海外世界的比较与前述他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关系
密切,两者背后都有寻找对中国现代性问题之回答的努力,并且与同时
代很多学者相似,一开始他的比较对象主要是英美。但不同的是,他的
比较研究没有停留在文化学的比较,而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观念
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与知识实践都有所涉及。若是将他所有关于海外
研究的论述集中在一起,那么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 1 1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