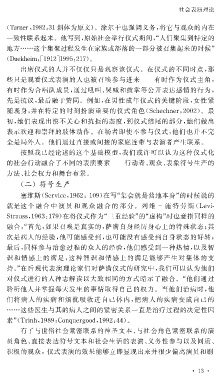Page 20 - 《社会》2015年第3期
P. 20
社会表演理论
( 犜狌狉狀犲狉 , 1982 : 31 斜体为原文)。涂尔干也强调义务,将它与观众的内在
一致性联系起来。他写到,原始社会举行仪式期间,“人们聚集到特定的
地方……这个集聚过程发生在家族或部落的一部分被召集起来的时候”
( 犇狌犲犽犺犲犻犿 ,[ 1912 ] 1995 : 217 )。
出席仪式的人并不仅仅只是观察该仪式。在仪式的不同时点,那
些只是观看仪式表演的人也被召唤参与进来———有时作为仪式主角,
有时作为合唱队成员,通过吼叫、哭喊和鼓掌等公开表达感情的行为,
先是抗议,最后融于赞同。例如,在男性成年仪式的关键阶段,女性紧
随现身,并在特定的时刻扮演重要的仪式角色( 犛犮犺犲犮犺狀犲狉 , 2002 )。最
初,她们表现出漠不关心和抗拒的态度,到仪式结尾的部分,她们做出
表示欢迎和崇拜的肢体动作。在场者即使不参与仪式,他们也并不完
全是局外人。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家庭连带与表演者产生联系。
按照我已经论述的这个基础模型,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种仪式化
的社会行动融合了不同的表演要素———行动者、观众、表象符号生产的
方法、社会权力和舞台布景。
(二)符号生产
塞维斯( 犛犲狉狏犻犮犲 , 1962 : 109 )在写“集会就是营地本身”的时候说的
就是这个 融 合 中 演 员 和 观 众 融 合 的 部 分。 列 维 - 施 特 劳 斯 ( 犔犲狏犻
犛狋狉犪狌狊狊 , 1963 : 179 )在将仪式作为“三重经验”的“虚构”时也意指同样的
融合:“首先,如果召唤是真实的,萨满自身经历身心上的特殊状态;其
次是病人的经验,他可能感受到,也可能没有感受到自身状态的好转;
最后,同样参与治愈过程的众人的经验,他们感受到一种热情,以及智
识和情感上的满足,这种智识和情感上的满足能够产生对集体的支
持。”在后现代表演理论家们对萨满仪式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认为他们
对仪式进行的人种志解读以大致相同的方式暗示了融合。“他们通过
聆听他人并掌握每天发生的事情取得自己的权力。当他们治病时,他
们将病人的疾病和烦扰吸收进自己体内,把病人的疾病变成自己的
……这些医生与其的病人之间的紧密关系一直是治疗过程的决定性因
素”( 犜狉犻狀犺 , 1989 ; 犆狅狀 狇 狌犲狉 犵 狅狅犱 , 1992 : 44 )。
有了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的神圣文本、与社会角色紧密联系的演
员角色、直接表达符号文本和社会生活的表演、义务性参与以及同质、
积极的观众,仪式表演的效果能够立即显现出来并很少偏离演员和剧
· 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