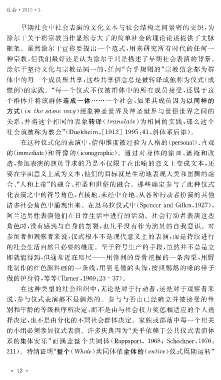Page 19 - 《社会》2015年第3期
P. 19
社会· 2015 · 3
早期社会中社会表演的文化文本与社会结构之间紧密的交织,为
涂尔干关于将宗教当作显然夸大了的简单社会的理论论述提供了文脉
框架。虽然涂尔干宣称要提出一个范式,用来研究所有时代的任何一
种宗教,但我们最好还是认为涂尔干只是描述了早期社会表演的背景。
涂尔干坚持文化与宗教是同一的,任何“合乎规则的”宗教信念都为群
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所共享,这些共享信念总是被转译成他称为仪式(或
惯例)的实践。“每一个仪式不仅被群体中的所有成员接受,还属于这
个群体并将该群体连成一体……一个社会,如果其成员因为以同样的
方式( 犻狀狋犺犲狊犪犿犲狑犪 狔 )想象神圣世界及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之间的
关系,并将这个相同的表象转译( 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 )为相同的实践,那么这个
社会就被称为教会”( 犇狌犲犽犺犲犻犿 ,[ 1912 ] 1995 : 41 ,斜体系后添)。
在这种仪式化的表演中,信仰维度被经验为人格的( 犲狉狊狅狀犪犾 )、直观
狆
的( 犻犿犿犲犱犻犪狋犲 )和符像的( 犻犮狅狀狅 犵 狉犪 狆 犺犻犮 )。通过对身体的涂画、遮掩和改
造,参加表演的演员寻求的乃是不仅限于在比喻的意义上变成文本,还
要在字面意义上成为文本,他们的目标就是生动地表现人类和图腾的融
合、“人和上帝”的融合、神圣和世俗的融合。那些确定参与了此种仪式
化表演之中的符号角色,直接地、未经中介地、从各种行动者扮演的其他
诸多社会角色中涌现出来。在恩乌拉仪式中( 犛 狆 犲狀犮犲狉犪狀犱犌犻犾犾犲狀 , 1927 ),
阿兰达男性表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活动。社会行动者表演这些
角色时,没有感到与自身的割裂,也几乎没有作为演员的自我意识。对
参加者和观察者来说,仪式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表演,而是持续进行
的社会生活自然且必要的维度。至于符号生产的手段,虽然并不总是立
即就能得到,但通常近在咫尺———用锋利的兽骨挖掘的一条沟渠,用野
花制作的红色颜料画的一条线,用羽毛做的头饰,按照鹦鹉的喙的样子
做的护身符,等等( 犜狌狉狀犲狉 , 1969 : 23-37 )。
在这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无论是对于行动者,还是对于观察者来
说,参与仪式表演都不是偶然的。参与与否由已经确立并被接受的性
别和年龄的等级秩序所决定,而不是由与社会权力奖惩相适应的个人选
择决定,也不是由分化的不同社会群体决定。家族或部落中每一个相关
的小组必须参加仪式表演。许多庆典因为“关乎依赖于公共仪式表演体
系的集体安乐”而涵盖整个共同体( 犚犪 狆狆 犪 狆 狅狉狋 , 1968 ; 犛犮犺犲犮犺狀犲狉 , 1976 :
211 )。特纳证明“整个( 犠犺狅犾犲 )共同体依全体的( 犲狀狋犻狉犲 )仪式周期运转”
·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