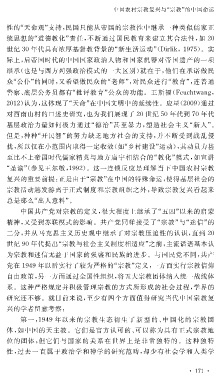Page 178 - 《社会》2019年第1期
P. 178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性的“天命观”支持,民国只能从帝国的宗教性中继承一种类似儒家正
统思想的“道德教化”责任,不断通过国民教育来建立其合法性,如 20
世纪 30 年代具有浓厚基督教背景的“新生活运动”( 犇犻狉犾犻犽 , 1975 )。实
际上,后帝国时代的中国国家政治人物和国家机器对帝国遗产的一项
继承(也是与西方列强政治模式的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在承诺做民
众“公仆”的同时,又希望做民众的“老师”,对民众进行“教育”,连普通
警察、底层公务员都有“批评教育”公众的功能。王斯福( 犉犲狌犮犺狋狑犪狀 犵 ,
2012 )认为,这体现了“天命”在中国文明中的延续性。应星( 2009 )通过
对西南山村的口述史研究,也为我们展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
基层政治力量如何极力通过“德治”甚至暴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但是,种种“开民智”的努力缺乏地方社会的支持,并不断受到战乱侵
扰,所以仅在小范围内取得一定收效(如“乡村建设”运动),其动员力甚
至比不上帝国时代儒家精英与地方庙宇相结合的“教化”模式,如宣讲
“圣谕”(参见王尔敏, 1992 )。这一连锁反应是理解当下中国农村宗教
复兴的重要前提:正是由于“宗教”在中国的特殊命运,使得基层社会的
宗教活动越发游离于正式制度和宗教组织之外,导致宗教复兴看起来
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定义,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以来的启蒙
精神,又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共产党同样接受了“宗教”与“迷信”的
二分,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继承了对宗教压迫性的认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之前,主流话语基本认
为宗教和迷信无益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进步。与国民党不同,共产
党在 1949 年以后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宗教”定义,一方面实行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全国性组织,将五大宗教团体纳入统一战线体
系。这种严格规定并积极管理宗教的方式所形成的社会过程,学界的
研究还不够。就目前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研究当代中国宗教复
兴的学者留意考察:
第一, 1949 年以来 的 宗 教 生 态 衍 生 了 新 型 的、中 国 化 的 宗 教 团
体,如中国的天主教。它们是官方认可的、可以称为具有正式宗教地
位的团体,但它们与 国 家 的关 系在 世界上 是非 常独特 的。这 种独特
性,过去一直 属 于政治学和神学的研究范畴,却少有社会学和人类学
· 1 7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