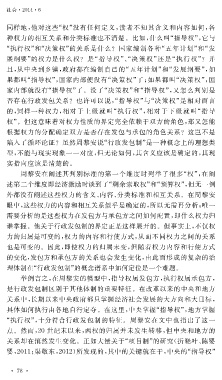Page 85 - 《社会》2014年第6期
P. 85
社会· 2014 · 6
同样地,他对这些“权”没有任何定义,读者不知其含义和内容如何,各
种权力的相互关系和分类标准也不清楚。比如,什么叫“指导权”,它与
“执行权”和“决策权”的关系是什么?国家编制各种“五年计划”和“发
展纲要”的权力是什么权?是“指导权”、“决策权”还是“执行权”?并
且,从中央到乡镇,政府都在编制自己的“五年计划”和“发展纲要”,如
果都叫“指导权”,国家内部便没有“决策权”了;如果都叫“决策权”,国
家内部就没有“指导权”了。没了“决策权”和“指导权”,又怎么判别是
否存在行政发包关系?也许可以说,“指导权”与“决策权”是相对而言
的,同样一种权力,相对于上级就叫“执行权”,相对于下级就叫“指导
权”。但这意味着对权力性质的界定完全依赖于双方的角色,那又怎能
根据权力的分配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发包与承包的角色关系?这岂不是
陷入了循环论证?虽然周黎安说“行政发包制”是一种概念上的理想类
型,不能与现实现象一一对应,但无论如何,其含义应该是确定的,其现
实指向应该是清楚的。
周黎安在阐述其判别标准的第一个维度时列举了很多“权”,在阐
述第二个维度即经济激励时谈到了“剩余索取权”和“预算权”,但无一例
外都没有阐述这些权力的含义、内容、分类标准和相互关系。在周黎安
眼中,这些权力的内容和相互关系似乎是确定的,所以无需再分析;唯一
需要分析的是这些权力在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如何配置,即什么权力归
谁掌握。他关于行政发包制的界定正是这样展开的。但事实上,不仅权
力的归属是可变的,权力的内容和行使方式,从而不同权力之间的关系
也是可变的。因此,即使权力的归属未变,但随着权力内容和行使方式
的变化,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由此而形成的复杂的治
理体制在“行政发包制”的概念谱系中如何定位是一个难题。
举例言之,在周黎安的模型中,指导权属发包方,执行权属承包方,
是行政发包制区别于其他体制的重要特征。在改革以来的中央和地方
关系中,长期以来中央政府都只掌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大目标,
具体如何执行由各地自行定夺。在这里,中央掌握“指导权”,地方掌握
“执行权”,十分符合行政发包制的特征。周黎安在文中也指出了这一
点。然而, 20 世纪末以来,两权的归属并未发生转移,但中央和地方的
关系却在悄然发生变化。正如大量关于“项目制”的研究(折晓叶、陈婴
婴, 2011 ;渠敬东, 2012 )所发现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央的“指导权”
·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