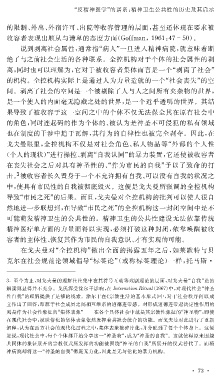Page 80 - 《社会》2014年第2期
P. 80
“反精神医学”的谱系:精神卫生公共性的历史及其启示
的限制、外出、外宿许可、出院等收容管理的层面,甚至还体现在要求被
收容者表现出顺从与谦卑的态度方面( 犌狅犳犳犿犪狀 , 1961 : 47-50 )。
说到剥离社会属性,通常指“病人”一旦进入精神病院,就意味着断
绝了与之前社会生活的各种联系。全控机构对于个体的社会属性的剥
离,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它对于被收容者集体而言是一个“剥离了社会”
的机构。全控机构实际上是通过人为力量造就的一个“社会丧失”的空
间。剥离了社会的空间是一个被剔除了人与人之间所有夹杂物的世界,
是一个使人的内面毫无隐藏之处的世界,是一个近乎透明的世界。其结
果导致了被收容于这一空间之中的个体不仅无法保全其在原有社会中
的角色,同时连起码的作为个体的、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领域
也在制度的干涉中趋于瓦解,其行为的自律性也被完全剥夺。因此,在
戈夫曼眼里,全控机构不仅是对社会角色、私人物品等“外部的个人性
(个人的现状)”进行操控、剥离“自我认同”的暴力装置,它还使被收容者
在丧失社会之后对具有神圣性的、“作为市民的自我”予以了致命的打
击。 3 被收容者长久置身于一个不允许拥有自我、可以没有自我的状况之
中,使具有市民性的自我被彻底毁灭。这便是戈夫曼所强调的全控机构
导致“市民之死”的后果。而且,戈夫曼对全控机构的批判可以使人很自
然地进一步联想到,在导致“市民之死”的全控机构这一封闭空间中是不
可能萌发精神卫生的公共性的。精神卫生的公共性建设无法依靠传统
精神医疗单方面的力量而得以实现,必须打破这种封闭,依靠唤醒被收
容者的主体性、恢复其作为市民的自我意识、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戈夫曼对“全控机构”做出全面的揭露五年之后,如莱默特与贝
克尔在社会规范论领域倡导“标签论”(或称标签理论)一样,托马斯·
3. 至今为止,对戈夫曼的理解往往集中在其符号互动等戏剧理论的层面,对戈夫曼“自我”论的
解读则显得并不充分。戈氏深受涂尔干影响,在犐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犚犻狋狌犪犾 ( 1967 )中,对现代社会“神圣
性自我”的理解提供了足够的线索。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于社会秩序何以成
立作出了回答,即源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维系的道德连带感。对形成道德连带起决定性作用的
则是作为社会性象征的“集体表象”———在各个具体社会中就是其宗教性象征的“神圣物”,即使
在现代社会中,被世俗化的集体表象依然发挥着其社会统合的功能。而戈夫曼对此进行了重新
解释,认为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集体表象被碎片化,并分配到了每个个体身上。这便
是说,现代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开始分享这一“神圣物”,成为“神圣的自我”。这就使得原来围绕
共同体的象征展开的宗教仪式所发挥的功能被围绕“神圣的自我”所展开的仪式替代了。而精
神病院却将这一“神圣的自我”彻底无力化,因此是无与伦比的暴力机构。
· 7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