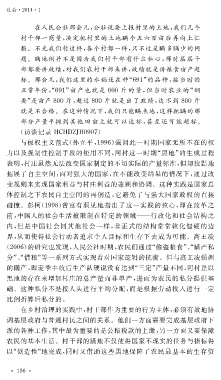Page 163 - 《社会》2014年第1期
P. 163
社会· 2014 · 1
在人民公社那会儿,公社说要上报村里的土地,我们几个
村干部一商量,决定把村里的土地瞒个五六百亩后再向上汇
报。不光我们村这样,各个村都一样,只不过是瞒多瞒少的问
题。瞒地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村干部有什么私心,那时层层干
部都要讲政绩,对我们农村干部来讲,政绩就是讲粮食亩产超
标。那会儿,我们这里的水稻还在种“ 691 ”的品种,按当时的
正常年份,“ 691 ”亩产也就是 600 斤的量,但当时农业的“纲
要”是亩产 800 斤,超过 800 斤就是出了政绩,达不到 800 斤
就是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瞒点地,这样把瞒的那
部分产量平摊到其他田亩上就可以达标,甚至还可能超标。
(访谈记录 犎犆犎犇犣犑犎0907 )
与极权主义范式(孙立平, 1996 )强调此一时期国家无所不在的权
力以及强制性控制手段的使用不同,河村这一时期“黑地”的生成过程
表明,村庄虽然无法改变国家制定的不切实际的产量标准,但却狡黠地
拓展了自主空间:面对强大的国家,在不能改变结果的情况下,通过改
变规则来实现国家利益与村庄利益的兼顾和协调。这种实践是国家总
体控制之下农民自主空间的再创造,它避免了与强大国家政权的直接
碰撞。彭柯( 1998 )曾富有洞见地指出了这一实践的核心,即在改革之
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被限制在特定的领域———行政化和社会结构之
内,但是中国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非正式的结构常常软化僵硬的边
界,从而使得社会行动者追求个人目标和生存下去成为可能。高王凌
( 2006 )的研究也发现,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们通过“偷盗粮食”、“瞒产私
分”、“借粮”等一系列方式实现着对国家逻辑的抗衡。但与高王凌强调
的瞒产,即麦季丰收后生产队硬说没有达到“三定”产量不同,河村是以
黑地的存在来增加村庄的总产量而非单产,进而为农民的私分提供基
础。这种私分不是按人头进行平均分配,而是根据劳动投入进行一定
比例折算后私分的。
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村干部作为重要的行为主体,必须有效地协
调基层政府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一方面需要完成基层政府下
派的各种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公粮税款的上缴,另一方面又要保障
农民的基本生活。村干部的瞒地不仅使得国家不现实的任务与指标得
以“创造性”地完成,同时又借助这些黑地保障了农民最基本的生存资
· 1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