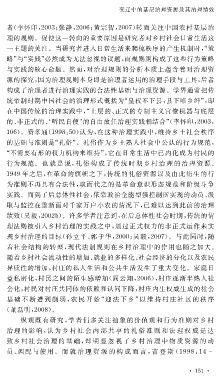Page 158 - 《社会》2014年第1期
P. 158
变迁中的基层治理资源及其治理绩效
者(李怀印, 2003 ;张静, 2006 ;黄宗智, 2007 )转而关注中国农村基层治
理的规则。促使这一转向的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对乡村社会日常生活这
一主题的关注。当研究者进入日常生活来爬梳秩序的产生机制时,“策
略”与“实践”必然成为无法忽视的议题,而规则则构成了这些行为策略
与实践的核心命题。然而,对治理规则的分析本质上蕴含着对治理资
源的探究,因为治理规则本身即是治理者运用的治理手段与工具,后者
构成了治理者进行治理实践的合法性基础与治理资源。学界通常把传
统帝制时期中国社会的治理形式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绅”,即
在中国传统的治理实践中,“上层的、正式的专制主义官僚机器与底层
的、非正式的、‘听民自便’的自由放任治理实践相结合”(李怀印, 2003 :
106 )。费孝通( 1998 : 50 )认为,在这种治理实践中,维持乡土社会秩序
的基础与准则是“礼俗”。礼俗作为乡土熟人社会中公认的行为规范,
“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它在日常生活中已内化成为村民的
行为规范。也 就 是 说,礼 俗 构 成 了 传 统 时 期 乡 村 治 理 的 治 理 资 源。
1949 年之后,在革命的旗帜之下,传统的礼俗资源以及由此衍生的行
为准则不再具有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意识形态规范和阶级斗争
实践。而到了后总体性社会,依靠政治全能型强控制所实现的动员、汲
取与监控在重新面对千家万户小农的情况下,已难以达到此前的治理
绩效(吴毅, 2002犫 )。许多学者注意到,在后总体性社会时期,传统的情
理法则被引入乡村治理的实践之中,通过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来实
现乡村治理的目标(孙立平、郭于华, 2000 ;吴毅, 2007 )。与此同时,随
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现代法制规则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也随之加大。
随着乡村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就业的多样化、社会经济的分化以及农民
异质性的增加,村庄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日
益私密化,村民之间的陌生感增加(阎云翔, 2006 ),村庄逐渐半熟人社
会化,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和认同下降,村庄内生权威生成的社会
基 础 不 断 遭 到 削 弱,农 民 开 始 “迎 法 下 乡”以 维 持 村 庄 社 区 的 秩 序
(董磊明, 2008 )。
纵观既有研究,学者们多关注抽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乡村
治理的影响,认 为 乡 村 社 会 内 部 共 享 的 礼 俗 准 则 和 法 理 权 威 是 达
致乡村社会治 理 的 基 础,却 明 显 忽 视 了 乡 村 治 理 中 物 质 资 源 的 动
员、调配与使用。而 就 治 理 资 源 的 构 成 而 言,吉 登 斯 ( 1998 : 14-
· 1 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