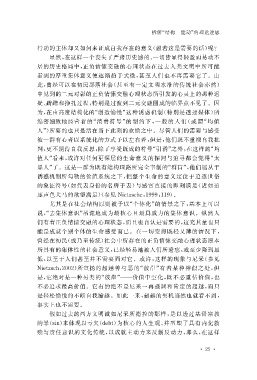Page 32 - 《社会》2013年第4期
P. 32
拆解“结构—能动”的理论迷思
行动的主体却又如何来证成自我存在的意义(假若这是需要的话)呢?
显然,在这样一个丧失了严肃历史感的、一切皆显得轻盈而易动不
居的历史格局中,正负情愫交融的心理状态在过去人类文明中所可能
看到的厚重集体意义便逐渐趋于式微,甚至人们也不再需要它了。由
此,曾经可以在初民部落社会(甚至有一定文明水准的传统社会亦然)
中见到的二元对彰的正负情愫交融心理状态所引发的心灵上的那种迟
疑、踌躇和挣扎过程,特别是过渡到二元交融圆成的临界点不见了。因
为,在由高度结构化的“制造愉悦”这种诱惑机制(特别是透过媒体)所
绵密细致地经营着的“消费符 号”的制 约下,一般 的人 们(或谓 “均 值
人”)所要的也只是活在当下此刻的欢愉之中。尽管人们的需要与感受
被一群有心者以系统化的方式予以左右着,但是,他们既不重视自我批
判,更不期待自我反思,除了享受既成的符号“引诱”之外,在这样的“均
值人”看来,或许对任何更深层的生命意义的探问与追寻都会觉得“太
累人”了。这是一群为既有结构理路所完全宰制的“群盲”,他们屈从于
诱惑机制所勾勒的价值系统之下,把整个生命的意义定位于追逐世俗
的象征符号(如代表身份的名牌手表)与感官直接的即刻满足(诸如追
逐声色犬马的欲望满足)(参见 犖犻犲狋狕狊犮犺犲 , 1999 : 119 )。
尤其是在社会结构原则被予以“个体化”的情景之下,基本上可以
说,“去集体意识”吊诡地成为最核心且最具威力的集体意识。纵然人
们有着正负情愫交融的心理状态,而且也自认是需要的,这充其量也只
能是成就个别个体的生命感受而已。在一切变得既轻又薄的情况下,
曾经在初民(或乃至传统)社会中所存在的正负情愫交融心理状态原本
所具有的集体性的社会意义,已经轻易地被人们所遗忘,或至少降到最
低,以至于人们甚至并不需要面对它。或许,这样的现象与尼采(参见
犖犻犲狋狕狊犮犺 , 2002 )所宣扬的超越善与恶的“彼岸”有着某种神似之处,但
是,它绝对是一种另类的“彼岸”———价值中空化,既不必重估价值,也
不必追求最高价值。它有的绝不是尼采一再强调和肯定的超越,而只
是轻松愉悦的不断自我?越。如此一来,超越的契机当然也就看不到,
事实上也不需要。
假如过去的西方文明诚如尼采所指控的那样,是以透过基督宗教
的罪( 狊犻狀 )来体现以亏欠( 犱犲犫狋 )为核心的人生观、并型塑了具有内化救
赎与责任意识的文化传统,以成就主动力来反制反动力,那么,在这样
· 2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