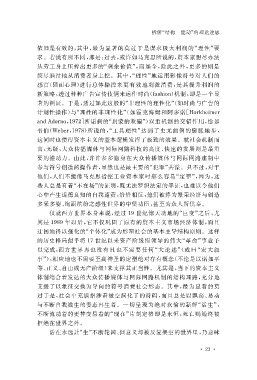Page 30 - 《社会》2013年第4期
P. 30
拆解“结构—能动”的理论迷思
依旧是有效的,其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是谋求极大利润的“理性”要
求。若说有所不同,那是:过去,或许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想尽办法
从劳工身上压榨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如今,除此之外,更多的则是
绞尽脑汁地从消费者身上挖。其中,“理性”地运用影像符号对人们的
感官(因而心理)进行总体操控来更有效地刺激消费,是其提升利润的
新策略,透过种种广告宣传伎俩来运作时尚( 犳犪狊犺犻狅狀 )机制,即是一个显
著的例证。于是,透过如此这般的“非理性的理性化”(如时尚与广告的
计划性操作)与“理性的非理性化”(如霍克海姆和阿多诺[ 犎狅狉犽犺犲犻犿犲狉
犪狀犱犃犱狅狉狀狅 , 1972 ]所诟病的“启蒙的欺骗”)双重机制的交错作用,恰如
韦伯( 犠犲犫犲狉 , 1978 )所说的,“工具理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膨胀地步,
这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发挥了极致的效果。就社会机制而
言,无疑,大众传播媒体与网际网路科技的高度、快速的发展则是最重
要的推动力。由此,许许多多隐身在大众传播媒体与网际网路建制中
参与符号创造的操作者,显然也是最主要的“犯罪”共谋。只不过,对于
他们,人们不能像马克思指控工业资本家时那么容易“定罪”,因为,这
些人总是有着“不在场”的证明,既无法罗织法定的罪证,也难以令他们
心中产生道德良知的自我谴责,恰恰相反,他们被捧为繁荣经济与创造
多采多姿、绚丽缤纷之感性世界的中坚功臣,甚至为众人所供奉。
仅就西方世界本身来说,经过 19 世纪惊天动地的“巨变”之后,尤
其是 1989 年以后,它不仅巩固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
迂回地得以强化的“个体化”成为形塑社会的基本主导结构原则。这样
的历史格局似乎将 17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予
以完成,西方世界再也没有且也 不需 要任何“大论述”(或 曰“宏大 叙
事”),相应地也不需要至高神圣的定型绝对存有概念(不论是以诸如平
等、正义、自由或无产阶级)来支撑其正当性。尤其是,当下的资本主义
体制结合着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体与网际网路机制的结构理路,充分地
支援了以象征交换为导向的符号消费社会形态。其中,最为显着的莫
过于是,社会中充满指涉着被空洞化了的符码,而且总是以飘荡、易动
与不断自我滋生的姿态再生着。一切呈现为绝对欢愉的新鲜“活生”,
不断流动着的更替变易着的“现在”片刻定格即是永恒,死亡则始终被
拒绝在世界之外。
活在永远让“生”不断轮回、但意义却被反复架空的世界里,乃意味
·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