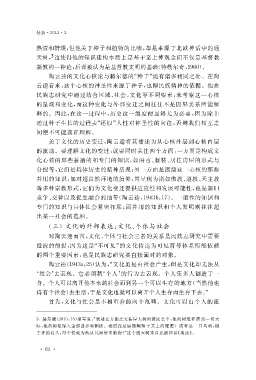Page 69 - 《社会》2013年第2期
P. 69
社会· 2013 · 2
热情和赞颂,但他关于种子和植物的比喻,却是来源于北欧神话中的通
天树, 3 这使得他的知识建构本质上是基于至上神观念而不仅是基督教
新教的一神论,后者被认为是基督教文明的基础(特勒尔奇, 1960 )。
陶云逵的文化心核论与赫尔德的“种子”说有诸多相同之处。在陶
云逵看来,这个心核的神圣性来源于种子,也即民族精神的依据。他在
民族志研究中通过结合区域、社会、文化等不同要素,来考察这一心核
的呈现和变化,而这种变化与外部变迁之间往往不是因果关系所能解
释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这一维度便显得尤为必要,因为除非
通过种子生长的过程去“还原”人性对神圣性的向往,否则我们相互之
间便不可能真正理解。
关于文化的历史变迁,陶云逵将其描述为从心核外层到心核内层
的流动。要理解文化的变迁,就要同时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构成文
化心核的那些普遍的和专门的知识,如语言、服装、居住房屋的形式与
分配等,它们是具体历史的精神呈现;另一方面是围绕这一心核的那些
并用的知识,如对超自然环境的信仰,其呈现为诸如佛教、道教、天主教
等多种宗教形式,它们为文化变迁提供适应性和发展可能性,也是新旧
竞争、交替以及促生融合的地带(陶云逵, 1943犫 : 17 )。一般性的知识和
专门的知识与具体社会紧密扣联;而并用的知识和个人发明则往往超
出某一社会的范围。
(三)文化的外部表达:文化、个体与社会
对陶云逵而言,文化、个体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民族志研究中需要
澄清的前提,因为这是“不可见”的文化传达为可见符号体系所能依赖
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民族志研究要直接面对的对象。
陶云逵( 1943犪 : 25 )认为,“文化虽是由社会产生,但是文化却无法从
‘社会’去表现。它必须藉‘个人’的行为去表现。个人集多人创造于一
身。个人可以离开他本来的社会而到另一个可以生存的地方(当然他也
得有个社会)去生活,于是文化也就可以离开个人生存而生存下去。”
首先,文化与社会是不相重合的两个范畴。文化可以由个人的流
3. 赫尔德( 2010 : 15 )描写道:“我站在万能之父伟岸大树的荫庇之中,他的树冠伸展到一切天
际,他的树根深入全部世界和渊极。难道我是展翅翱翔于其上的雄鹰?或者是一只乌鸦,栖
于神的肩头,每个傍晚为他从凡间带来献物?”这个通天树来自北欧神话《埃达》。
· 6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