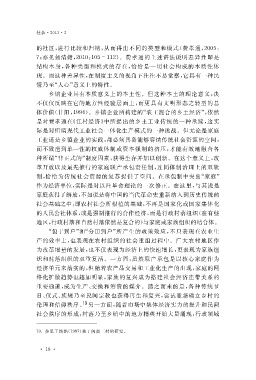Page 25 - 《社会》2013年第2期
P. 25
社会· 2013 · 2
的社区,进行比较和归纳,从而得出不同的类型和模式(费孝通, 2005 :
7 ;亦见杨清媚, 2010 : 105-112 )。费孝通的上述讲法说明差异性即是
结构本身,各种类型和模式的存在,恰恰是一切社会构成的本质性体
现。而这种差异性,在制度主义的视角下往往不易觉察,它具有一种民
情乃至“人心”意义上的特性。
乡镇企业具有本质意义上的本土性。但这种本土的理论意义,决
不仅仅反映在它的地方性经验层面上,而更具有文明形态之转型的总
体价值(甘阳, 1994 )。乡镇企业所构建的“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依然
是对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所提出的乡土工业传统的一种承续,这实
际是对所谓现代工业社会一体化生产模式的一种挑战。但无论是家庭
工业还是乡镇企业的实践,都必须具备能够容纳传统社会资源的空间,
而不致遭到单一性的权威体制或资本强制的挤压,才能有效地融合各
种所谓“非正式的”制度因素,获得生存并加以创新。在这个意义上,改
革开放以及最先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同体制治理上的双轨
制,恰恰为传统社会资源的复苏提供了空间。在承包制中突出“家庭”
作为经济单位,实际是对以往革命理论的一次修正。在这里,与其说是
家庭获得了解放,不如说是将中国的当代革命史重新纳入到历史传统的
社会基础之中:即农村社会所根植的基础,不再是国家化或国家集体化
的人民公社体系,或是强制推行的合作经济,而是行政村落组织(在有些
地区,行政村落和自然村落依然是复合的)与家庭或家族组织的结合体。
“包干到户”和“分田到户”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不只表现在农业生
产的效率上,也表现在农村组织的社会重组过程中。广大农村地区作
为改革增量的发展,也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快速增长,更表现为家族组
织和村落组织的双重复活。一方面,虽然联产承包是以核心家庭作为
经济单元来落实的,但随着农产品交易和工业化生产的出现,家庭的网
络化扩散趋势也越加明显,家族的复兴成为搭建社会经济连带关系的
重要通道,成为生产、交换和筹资的媒介。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传统节
日、仪式、族规乃至民间宗教也获得再生和复兴,尝试重新确立乡村的
伦理和信仰秩序。 19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中集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民间
社会秩序的形成,村落乃至乡镇中的地方精英开始大量涌现,行政领域
19. 参见王铭铭( 1997 )关于闽南三村的研究。
· 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