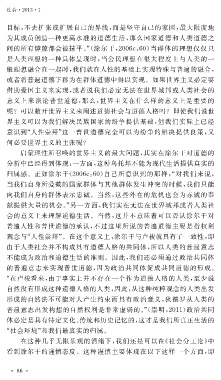Page 93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93
社会· 2013 · 1
目标,不去扩张或扩展自己的界线,而是坚守自己的家园,最大限度地
为其成员创造一种更高水准的道德生活,那么国家道德和人类道德之
间的所有罅隙都会被抹平。”(涂尔干, 2006犮 : 60 )当群体的理想仅仅只
是人类理想的一种具体呈现时,当公民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一
般理想融合在一起时,我们就在人性的基础上实现特殊与普遍的融合,
或者将普遍道德下移为在群体道德中得以实现。如果世界主义必定要
借助爱国主义来实现,或者说我们必定无法在世界城邦或人类社会的
意义上来谈论普世道德,那么,世界主义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是重要的
呢?可以敝开世界主义来阐述道德社会与道德人格吗?即使我们说世
界主义可以为我们解决民族国家的纷争提供基础,但我们实际上已经
意识到“人性崇拜”这一普世道德完全可以为纷争的解决提供良策,又
何必要世界主义的主张呢?
启蒙理性所召唤的世界主义的最大问题,其实在涂尔干对道德的
分析中已经得到体现:一方面,这种乌托邦不能为现代生活提供真实的
归属感。正如涂尔干( 2006犮 : 60 )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
当我们自身所爱戴的国家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只能
向我们自身的群体表示忠诚。当然,这些外在的危机也会为赤诚的奉
献提供大量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实在无法在世界城邦或者人类社
会的意义上来理解道德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涂尔干对
普遍人性和普世道德的承认,不过这里所说的普遍道德主要是指权利
观念与“人性崇拜”。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与卢梭就具有了一致性,即
由于人类社会并不构成具有道德人格的共同体,所以人类的普遍意志
不能成为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准则。因此,我们还必须通过政治共同体
的普遍意志来实现普世道德,因为政治共同体促成共同道德的形成。
“ 在卢梭看来,由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作为道德人格的人类,至少说
自然没有形成这种道德人格的人类,因此,从这种纯粹观念的人类出发
形成的自然法不可能对人产生约束而具有政治意义,狄德罗从人类的
普遍意志出发构想的自然权利是非常虚弱的。”(崇明, 2011 )政治共同
体必定是具有特定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这才是我们所真正生活的
“社会环境”和我们最真实的归属。
在这种几乎无限乐观的情绪下,我们还是可以在《社会分工论》中
看到涂尔干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主要体现在以下这样一个方面,即
· 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