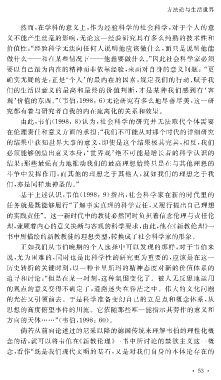Page 60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60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然而,在学科的意义上,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对于个人的意
义不能产生丝毫的影响,无论这一经验研究具有多么纯熟的技术性和
价值性:“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
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因此社会科学家必须
要以自己最为内在的精神而非依靠经验,来面对自身的意义问题:“更
确实无疑的是: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
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
观’价值的东西。”(韦伯, 1998 : 6 )无论研究有多么地尽善尽美,这一研
究都有着与研究者自我的内在疏离化的关系和效果。
由此,韦伯( 1998 : 8 )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无法取代个体需要
在伦理责任和意义方面的承担:“我们不可能从对那个时代的详细研究
的结果中获知世界大事的意义,即使是这个结果极其完善,相反,我们
獉獉
必须能够创造出意义本身;‘世界观’绝不可能是增长着的科学认识的
结果;那些最强有力地推动我们的最高理想始终只是在与其他理想的
斗争中发挥作用,而其他的理想之于其他人,就如我们的理想之于我
们,亦是同样地神圣的。”
基于上述认识,韦伯( 1998 : 9 )指出,社会科学家在新的时代里的
任务就是既能够履行“了解事实真理的科学责任,又履行提出自己理想
的实践责任”。这一新时代中的教徒必然同时负担着信念伦理与责任伦
理,兼顾着内心的意义决断与客观的科学要求,由此,他在《新教伦理》一
书中所描绘的新教教徒的理想类型,转换成了社会科学家的形象。
正如我们从韦伯晚期的个人选择中可以发现的那样,对于韦伯来
说,尤为困难的,同时也是比科学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在这一
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一种卡里斯玛的精神态度对新的价值体系的
追寻和讨论:“但是在某一时刻,这种氛围变化了。被人无反思地运用
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确定了,道路迷失在昏茫之中。伟大的文化问题
的光芒又引领前去。于是科学准备变幻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
思想的高度俯望事件的川流。它依随那些唯一能指示其劳作的意义和
方向的天体……”(韦伯, 1998 : 60 )。
倘若从前面论述过的尼采以降的德国传统来理解韦伯的理性化概
念的话,就可以将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讨论的禁欲主义这一概
念,看作“既是我们现代文明的基石,又是对我们自身的本体论存在的
· 5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