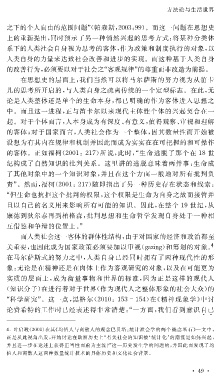Page 56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56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之下的个人自由的范围问题”(帕森斯, 2003 : 99 )。而这一问题在思想史
上的重新提出,同时预示了另一种悄然兴起的思考方式:将某种分类体
系下的人类社会自身视为思考的客体,作为政策和制度执行的对象,以
人类自身的力量来达致社会改善和进步的实现。而这种基于人类自身
的改善行为,必须要以对于社会之“客观规律”的尊重而非改造为前提。
在思想史的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将马尔萨斯的努力视为从笛卡
儿的思考所开启的,与人类自身之疏离传统的一个定型标志。在此,无
论是人类整体还是单个的生命本身,都已明确的作为客体进入思想之
中。而且这一进程,正与笛卡尔以来现代主体性个体的兴起契合在一
起。对于个体而言,人本身成为有深度、有意义,值得观察、审视和理解
的客体;对于国家而言,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因其数量性而开始被
设想为有其内在规律和机制并因此而成为实实在在可把握的和可操作
的客体。正如福柯( 2001 : 217 )所说,此时,“生命逃脱了那个在 18 世
纪构成了自然知识的批判关系。这里讲的逃脱意味着两件事:生命成
了其他对象中的一个知识对象,并且在这个方面一般地对所有批判负
责”。然而,福柯( 2001 : 217 )随即指出了另一种历史存在状态和线索:
“ 但生命也抗拒这个批判的权限,这个权限是生命为自身之故而接管并
且以自己的名义用来影响所有可能的知识。因此,在整个 19 世纪,从
康德到狄尔泰再到柏格森,批判思想和生命哲学发现自身处于一种相
互借鉴和争辩的位置上。”
而人类社会这一客体的群体性结构,由于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至
关重要,也因此成为国家政策必须要加以审视( 犪狕犻狀 犵 )和筹划的对象。 4
犵
在马尔萨斯式的努力之中,人类自身已经同时拥有了两种现代性的形
象:无论是在精神还是在肉体上作为客观研究的对象,以及在可能更为
实质的层面上,成为衡量事物和世界的标准,因为正是这样的现代人
(知识分子)在进行着对于世界(作为现代人之整体形象的社会大众)的
“科学研究”。这一点,黑格尔( 2010 : 153-154 )在《精神现象学》中讨
论费希特的工作时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一方面,我们看到意识自己
獉獉
4. 叶启政( 2001 )在其《均值人与离散人的观念巴贝塔:统计社会学的两个概念基石》一文中,
正是从此视角出发,开始讨论在欧洲历史上“有关社会的知识被‘统计化’的潮流是如何兴起,
并且进一步在论述上获得正当性而蔚为主流?”这一历史发生学的问题的,并因此而发现了均
值人和离散人这两种数量统计技术的具体历史和文化社会背景。
· 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