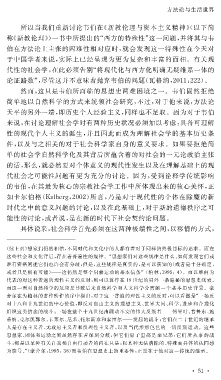Page 58 - 《社会》2013年第1期
P. 58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所以当我们重新讨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
称《新教伦理》)一书中所提出的“西方的特殊性”这一问题,并将其与韦
伯在方法论上主张的两难性相对应时,就会发现这一特殊性在今天对
于中国学者来说,实际上已经呈现为更为复杂和丰富的面相。有关现
代性的社会学,在此必须告别“将现代化与西方化明确无疑维系一体的
论证路数”,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抛弃韦伯的问题(瓦格纳, 2011 : 222 )。
然而,这只是韦伯所面临的思想史两难困境之一。韦伯固然拒绝
简单地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统领社会研究,不过,对于他来说,方法论
天平的另外一端,即历史个人经验主义,同样也不足取。因为对于韦伯
来说,在讨论理解社会学时有两种历史状况必须加以考虑:具备可理解
性的现代个人主义的诞生,并且因此而成为理解社会学的基本历史条
件,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于社会科学家自身的意义要求。如果要拒绝简
单的社会学自然科学化及其背后所蕴含着的对社会的一元论政治主张
的话,那么,就必然要对个体意义的现代性发生以及在理解基础上的现
代社会之可能性问题有更为充分的讨论。因为,受到诠释学传统影响
的韦伯,在其最为核心的宗教社会学工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核心关怀,正
,
如卡尔伯格( 犓犪犾犫犲狉 犵2002 )所言,乃是对于现代性的个体在除魔的新
时代之中的意义问题的讨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新的道德秩序之可
能性的讨论,或者说,是在新的时代下社会契约论问题。
具体说来,社会科学首先必须在这两种极端性之间,以移情的方式,
(续上页)想家们仍然相信,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人都有着对于同样的终极目标的追求。而在
这些社会和文化背后,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律。“思想家们对这些规律是什么、如何发现它们或
谁有资格阐述它们也许会有分歧;但是,这些规律是真实的,是可以获知的(或者是十分确定,
或者只是极有可能)———这仍然是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柏林, 1995 : 4 )。而以维柯为
代表的对这种普遍的理性主义的反对,则可以算作在 19 世纪的另外一条隐秘的思想史线索。
而这一面对自然科学的反应是导致后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豪
舍尔在为柏林的著作所作的序中指出,对于这一普遍的理性主义的反对,可以看做是“一场反
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中心价值,即反对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世界大同、科学、进步和合理化
组织这类信念的战斗:一场在整个十九世纪由躁动不安的伟大反叛者———傅里叶、普鲁东、施
蒂纳、克尔凯郭尔、卡莱尔、尼采、托尔斯泰和索雷尔———发起的战斗;它们在二十世纪的继承
人是存在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反理性主义者,以及当代形形色色的一切反叛运动。这些
思想家、团体和运动之间虽然存在着深刻分歧,但它们骨子里都是亲兄弟:它们所从事的战
斗,都是以某种有关自我和自由行动者的内在只是,以某种无法消除的、特殊而具体的认同感
为旗号。”(豪舍尔, 1995 : 38 )而韦伯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对这一传统的继承。
· 5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