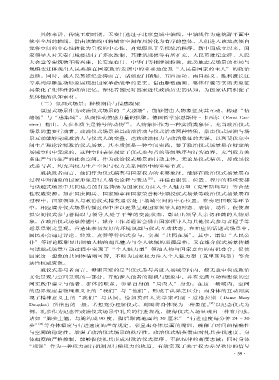Page 61 - 《党政研究》2025年第3期
P. 61
具体来讲,传统王朝时期,天安门选址于北京皇城中轴线,中轴线作为建筑群平面中
统率全局的轴线,借由该轴线可将城市空间布局转化为有序的整体,人们进入该地点便自
觉将空间的中心性转化为皇权的中心性,自觉服从于皇权统治秩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家领导人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多次改制,其建筑规模等有所扩充,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
大会堂等建筑物不断兴建,长安左右门、中华门等相继被拆除,此类地志式场景的布局与
规模变迁体现出人民英雄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政治
意涵。同时,就人民英雄纪念碑而言,诸如虎门销烟、五四运动、南昌起义、胜利渡长江
等系列浮雕生动形象展现出国家革命战争的史实,借由雕塑画面、整体样貌等实质类象征
具象化了集体性的政治记忆,深化着国民对国家近代政治历史的认知,为国家认同积淀了
集体性的认知素材。
(二)氛围式场景:楷模期待与情感凝聚
氛围式场景作为政治仪式场景的 “大剧场”,能够借由人物象征及其互动,构建 “情
绪场”与 “感染域”,从而推动情感力量的积聚。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 Ernst Cas
sirer)指出,人在本质上是符号的动物 。人物象征作为一种实质类象征,充当政治仪式
〔 25〕
场景的重要行动者。政治仪式场景兼具政治活动与仪式活动两种特质,借由仪式展演与场
景互动能够完成政治人与仪式人的交叠,达致政治权力与政治象征的共谋。以列斐伏尔空
间生产理论诠释政治仪式场景,其本质便是一种空间实践,鉴于政治仪式场景是在特定的
场域空间中完成的,这种空间表征规定了仪式参与者的等级秩序与行为边界,充当权力关
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作为政治仪式场景的行动主体,无论是仪式精英,抑或是仪
式参与者,均充当权力生产空间与权力关系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就执政者而言,他们作为仪式精英与国家权力的重要象征,能够在政治仪式场景展布
过程中对抽象的国家形象进行人格化诠释与表达 ,并借由服装、位置、程序的特殊安排
〔 26〕
与话题式场景中共同焦点的打造持续为国家权力注入个人魅力型 (克里斯玛型)等合法
性权威资源。如在国庆阅兵、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场景等政治仪式场景展布
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与政治仪式精英通常处于场域空间的中心位置。在奏唱国歌等环节
中,相应媒介仪式场景传播过程中多以近景呈现国家领导人的神态、表情、动作,促使虚
拟空间仪式参与者得以与领导人处于平等的交流状态,彰显出领导人亲切和蔼的人物形
象。在政治仪式场景传播中,媒介工作者通常会借由国家领导人与其他仪式参与者握手等
近景景别之呈现,营造出亲切友好的环境氛围与仪式互动状态。在相应的话题式场景中,
国民亦会通过评论、转发、点赞等符码式参与,实现 “共同在场”。其中,诸如 “人民公
仆”等评论既彰显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与令人钦佩的道德品格,又在媒介仪式场景传播
与话题式场景互动过程中实现了 “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与国家意向的有机叠合,促使
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清晰可辨,不断为国家权力注入个人魅力型 (克里斯玛型)等合
法性权威资源。
就仪式参与者而言,毋庸置疑的是当仪式参与者进入场域空间内,便无意中构成政治
文化景观与空间景观的一部分,开始涉入他者的凝视与想象中,并在充满互动和想象的空
间实践中建立与他者、群体的联系,彰显自身的 “局内人”身份。在这一场域内,空间
的边界规定着物理意义上的 “我们”与 “他们”,形成了认异之区分;而身体的互动则实
现了精神意义上的 “我们”与认同。恰如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 Dame Mary
Douglas)所指出的一般,若想充分理解仪式,则需将身体视为一种象征。 以纪念仪式为
〔 27〕
例,礼步作为纪念性政治仪式场景中礼兵的行进规范,使得仪式入场显现出一种有序感。
诸如 “脚尖上翘,与腿约成 90 度,脚后跟离地面约 30 厘米” “行进速度每分钟 24 - 30
步” 等身体幅度与行进速度的严苛规定,彰显出身体层面的规训,确保了时间的精确性
〔 28〕
与空间的稳定性,增强了政治仪式场景的秩序性。政治仪式精英借由对礼兵步伐速度、身
体幅度的严格控制,能够促使礼兵形成对政治仪式程序、军队纪律的高度忠诚;同时身体
“规训”作为一种权力运行机制及行使权力的轨道,有效实现了关于权力差异秩序的信号
9 ·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