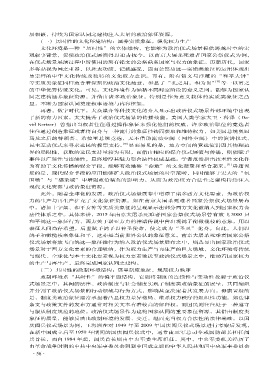Page 58 - 《党政研究》2025年第3期
P. 58
层相嵌,持续为国家认同之建构注入大量的政治象征资源。
(一)历时性的文化环境结构:涵养实质象征,强化权力生产
文化环境是一种 “历时性”的立体结构,它能够为政治仪式场景提供跨越时空的宏
观叙事背景,促使政治仪式展演得以追古抚今。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例,
在仪式场景展演过程中所使用的刻有铭文的公祭鼎系国家与权力的象征。历朝历代,国家
多将鼎视为国之重器,以旌表功绩,记载盛况,因而公祭鼎这一实质类象征的运用体现出
鼎崇拜的中华文化传统及独特的文化权力意识。再有,附有铭文与浮雕的 “和平大钟”
等实质类象征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蕴意,彰显了 “礼之用,和为贵” 等一以贯之
〔 19〕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见,文化环境作为涵括不同时空阶段的意义之网,能够为国家认
同之建构涵养象征资源,并借由诸多政治象征,特别是作为意义载体的实质类象征之凸
显,不断为国家认同奠定叙事语境与内容框架。
再者,数字时代下,大众媒介等科技文化的介入显示出政治仪式场景外部环境中出现
了新的有力因素,大大提升了政治仪式场景的传播效能。美国人类学家大卫·科泽 ( Da
vid Kertzer)曾指出当权者往往通过操作象征来强化他们的权威,许多政治职位的竞选者
往往通过创造象征或者将自身与一种流行的象征挂钩而获取和维持权力,如美国总统奥巴
马及之后的特朗普、希拉里总统竞选,无不借助流动空间 (网络空间)中的演讲仪式、
民主互动仪式来寻求选民的投票支持。 显而易见的是,地方空间的竞选演讲因其物理边
〔 20〕
界的局限性,获取的选民支持量较为有限,而借由相应的媒介仪式展演与传播,则能赋予
事件以广延性与连续性,最终增厚其魅力型合法性权威基础。学者范俊指出技术性文化作
为有助于文化传播的媒介手段,能够有效地将 “弥散”的文化凝聚和整合起来。 毋庸置
〔 21〕
疑的是,现代媒介手段的应用能够扩大政治仪式场景的时空范畴,同时能够于宏大的 “氛
围场”与 “感染域”中增强政治精英的影响力,从而为政治权力合法性之建构持续注入
现代文化资源与政治象征资源。
此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仪式场景展布中增添了诸多西方文化要素,为政治权
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扩充了文化象征资源。如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场景展布
中,诸如十字架、和平女神等实质类象征的呈现显示出部分西方文化被纳入到国家权力合
法性体系之中。具体来讲,2015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场景曾有放飞 3000 只
和平鸽这一象征行为,西方关于诺亚方舟的神话传说中曾出现鸽子衔橄榄枝的意象,用以
表征人间尚存希望。后世赋予鸽子以神圣使命,使之成为 “圣灵”化身。自此,人们以
鸽子和橄榄枝来象征和平,这亦是当前世界公认的象征意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场景将放飞白鸽这一象征性行为纳入政治仪式场景展布之中,则凸显出国家政治仪式
场景对于西方文化要素的合理吸纳,作为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巨大场域,文化环境将传统
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文化要素视为权力要素输送至政治仪式场景之中,推动着国家权力
的生产与再生产,最终完成国家认同之建构。
(二)共时性的政制环境结构:展呈制度象征,规范权力秩序
政制环境系 “共时性”的偏平面结构,它能将制度的连续性与变动性投射于政治仪
式场景之中,其间的法律、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实现了制度类政治象征的展呈,共同编织
并分割了政治仪式场景的行动领域与行为方式,影响甚至决定着其发展方向。毋庸置疑的
是,制度类政治象征通常承担着凸显权力差异格局、维系权力秩序的组织性功能。如法律
条文与政策文件的发布方通常对相关文本有着较高的解释权,而国民则往往处于一种遵守
与服从制度规范的地位。政治仪式场景作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源,其借由制度类
象征的展呈,能够反映出政制环境的发展、变迁,继而充当权力合法性的法律基础。以国
庆阅兵仪式场景为例,王海洲在对 1949 年至 2009 年国庆阅兵仪式场景进行考察后发现,
在新中国成立后至 1959 年期间的国庆阅兵仪式中,通常由三军总司令或国防部长担任阅
兵首长,而自 1984 年起,阅兵首长则由中央军委主席担任。其中,中央军委机关经历了
由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6 ·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