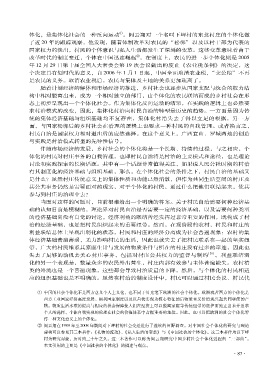Page 89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P. 89
体化,是集体化社会的一种反向运动 。阎云翔对一个名叫下岬村的东北村庄的个体化做
①
了近 20 年的跟踪观察,他发现,随着体制改革对农民的 “松绑”以及以村干部为代表的
国家权力的淡出,村民的个体意识与私人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意味着由于
②
改革时代的制度变迁,个体在中国迅速崛起 。在制度上,农民的进一步个体化则是 2005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9 次会议做出的废止 《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这
个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交公粮”不再
是农民的义务。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与集体及土地的关系更加疏离了。
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乡村社会也逐步从国家支配与统合的权力结
构中相对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由个体化的农民联结而成的乡村社会在形
态上初步呈现出一个个体化社会。作为集体化反向运动的结果,在实践的逻辑上也必然要
求村治模式的改变,因此,集体化村治向村民自治的转型是历史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传
统的集体经济基础与组织基础均不复存在,集体化村治失去了得以立足的根据,另一方
面,与国家松绑后的乡村社会在治理的逻辑上也要求一种村民的自我管理。或者换言之,
村民自治是国家权力相对退出后的应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广西宜山、罗城两地的创造
与实践是村治模式转型的先导性信号。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社会的个体化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与之相应,个
体化的村民对村庄事务的自我管理,也即村民自治将是村治的主要模式和途径,也是理论
讨论和实践探索的长期话题。其中有一个话题非常值得关注,如果说人民公社时期的村治
有其制度化的经济基础与组织基础,那么,在个体化社会的条件之下,村民自治的基础又
是什么?虽然村庄传统意义上的集体性质和功能已然消散,但作为共同生活空间的村庄及
其公共事务仍然是需要面对的现实,对于个体化的村民,通过什么把他们联结起来,使其
参与到村庄的治理中去?
当面对这样的问题时,目前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关于村民自治需要何种经济基
础的认知目前是模糊的,理论界对村民自治是否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需要何种类型
的经济基础尚没有自觉的讨论。经济利益的联结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既构成了村
治的经济基础,也是把村民组织起来的重要纽带。然而,在现阶段的农村,村民和村庄的
利益联结总体上呈现出弱化的状态,村民和村庄的经济分离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农村的集
体经济基础普遍薄弱,无力影响村民的生活,因此也就失去了把村民联系在一起的坚实纽
带,广大的村民维系其家庭生计与发展的物质条件与所在的村庄没有过多的牵连,因此也
失去了足够的动机去关心村庄事务,包括对村庄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利益联结弱
〔 20〕
化的另一个表现是,数量众多的农民外出营生,村庄内部有效参与主体普遍缺失。农村精
英的外流也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都会导致村治质量的下降。然后,与个体化的村民相适
应的组织基础也是不明确的。虽然在村治的制度设计中,村民可以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
① 中国的社会个体化不是西方意义个人主义化,也不同于贝克笔下欧洲的社会个体化。欧洲或者西方的个体化是
西方工业国家经济高度发展、福利国家制度以及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特征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共同驱使的产
物。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与相应的社会保障使人们在经济上可以脱离家庭等传统纽带的庇护而独立出来并追求
个人的选择,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可以把欧洲的社会个体化看
作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个体化。
② 阎云翔在 1989年至 2008年期间对下岬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连续的田野调查。对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研究与理论
建构可以参见其三本著作:《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与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这三本著作均以下岬
村为研究对象,历时约二十年之久。这三本著作可以称为阎云翔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个体化进程的 “三部曲”。
本文引用的主要是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的描述与观点。
7 ·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