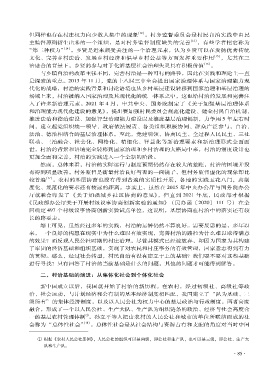Page 87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P. 87
但同样也存在村庄权力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民自治实践中由民
〔 12〕
主监督原则衍生出来的一个组织,是对村务监督制度缺失的完善 ,有些学者把它称为
〔 13〕
“第三种权力” 。乡贤是近来颇受关注的一个治理元素,认为乡贤可以在发扬优秀传统
〔 14〕
文化、完善乡村法治、发展乡村经济和倡导乡村公益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在三
〔 15〕
治融合的背景下,乡贤的参与对于化解基层社会治理失灵具有积极价值 。
〔 16〕
与乡镇自治的改革主张不同,完善村治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因此在实践和理论上一直
是探索的重点。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战略,村治的实践背景和讨论语境也从乡村基层建设转移到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
场域上来,村治被纳入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统一体系之中,这也给村治的发展和完善注
入了许多新治理元素。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强村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推进法治和德治建设、加强智慧治理能力建设以及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力争用 5 年左右时
间,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至此,党建引领、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三社
联动、三治融合、社会化、网格化、精细化、智慧化等新治理要素和新治理形式全面面
世,村治的背景和语境完全转移到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的大格局中来,村治的制度设计也
更加全面和完善,村治的实践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总体来看,村治的实际运行与制度预期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村治的困境并没
有得到明显改善。村务监督是衡量村治良好与否的一面镜子,但村务监督虚化的现象却比
较普遍 。农村的基层协商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质性开展,各地的实践五花八门,离制
〔 17〕
度化、规范化的要求还有较远的距离。事实上,虽然在 2015 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
厅就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但直到 2021 年底,民政部才根据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的通知》 (民办函 〔 2020〕111 号)在全
国确定 497 个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这说明,基层协商在村治中的落实还有较
长的路要走。
综上可见,虽然经过多年的实践,村治的运转仍然不算良好。需要反思的是,多年以
来,一个良好的构想在现实中为什么难以有效实现,完善村治的路径为什么难以取得满意
的效果?而反观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治理,尽管其模式已经被放弃,却因为国家为其构建
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实现了对农民和村庄事务的有效管理,国家意志得到有力
的贯彻。那么,经过社会转型,村民自治有没有建立于上的基础?我们要不要对这些基础
进行寻找?只有回答了村治的当前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其他的问题才可能得到解答。
二、村治基础的演进:从集体化社会到个体化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就开始了村治的新历程。在农村,经过初级社、高级社等政
治、社会运动,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匹配,我国建立了 “队为基础、三
级所有”的集体经济制度,以及以人民公社为权力中心的基层政治与行政制度,两者高度
融合,形成了一个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组织链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高度合
一的基层农村管理体制 。孙立平等人把由农村的人民公社和城市的单位所联结而成的社
①
会称为 “总体性社会” 。总体性社会是从社会结构与资源占有和支配的角度对当时中国
〔 18〕
① 根据 《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
队和生产队。
5 · ·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