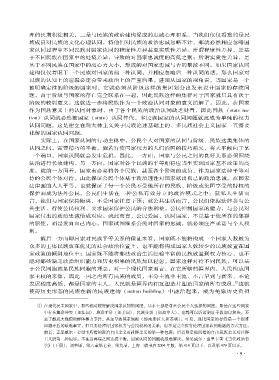Page 11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P. 11
理的长期积淀相关,二是与民族的政治建构促成的忠诚心理相系。当我们仅仅看重的是民
族成员对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将他们对民族的政治忠诚忽略不计,那就必然相应忽略国
家认同过程中不同民族对国家认同的程度性差异甚至实质性差异。所谓程度性差异,是基
于不同民族在国家中的处境差异,导致的对国家忠诚度的高低之别;所谓实质性差异,是
基于不同民族在国家中的离心力大小,形成的对国家忠诚与否的聚散不同。如果国家认同
建构仅仅着眼于一个民族对国家的前一种认同,并相应忽略后一种认同的话,那么国家对
民族的认知上的遗漏必定会带来政治上的严重后果。进而从国家的视角看,当国家是一个
被明确定性的阶级的国家时,它就必须从阶级这样的集团划分出发来设计国家的存续问
题,由于阶级与国家的存亡完全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这样的集群对于国家就只具有次于
阶级的较弱意义。这就进一步将民族作为一个政治认同对象的意义消解了。因此,在国家
作为国族意义上的认同对象时,由于各个民族的政治认同缺乏处置,因此国族 ( state na
tion)认同就必然被国家 ( state)认同替代。多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就此成为单纯的权力
认同问题。这是建立在斯大林主义关于民族论述基础上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需要
化解的国家认同问题。
实际上,在国家认同的行动主体中,公民个人对国家的认同与阶级、民族这类集体的
认同之间,需要精巧的平衡。倘若行使国家权力的人们治国的技巧稍欠,将天平倾向于某
一个端口,国家认同就会发生危机。因此,一方面,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必须围绕
法治进行长效建构。另一方面,国家对各个民族的平等相待应当坐实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
度。就前一方面看,国家有必要将各个民族,甚至各个阶级的成员,作为国家法律平等对
待的公民个体对待。由此保证公民个体基于政治理性对国家献出自己的政治忠诚。在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保证了每一个公民不受他所在的民族、阶级或集团享受的特权的
保护而成为法外公民。公民们生活在一种公私有效分立的政治模式之中:就私人生活而
言,他们与国家保持距离,不受国家任意干预;就公共生活而言,公民们依据法律参与公
共生活、行使公民权利、要求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公民控制国家的能力,与公民对
国家付出的政治忠诚恰成对应。就此而言,公民爱国、认同国家,不是基于他所在的集群
的驱使,而是发自自己内心。国家试图维系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就必须庄严承诺与个人权
利。
就后一方面即国家对民族平等关系的保证来看,国家既不能将构成一个国家人数最为
众多的主体民族放在优先的社会政治位置上,也不能将构成国家人数较少的民族放置在国
家政策的倾斜地位中;国家既不能将那些政治生活经验丰富的民族放置到权力核心,也不
能对那些缺乏政治组织能力和历史积累的民族加以轻忽。国家这样对待不同民族,可以基
于公民同胞就是民族同胞的理念,对一个现代国家而言,在它所辖的疆界内,人民构成国
家主权的来源,因此一国之内所有民族的成员,不分主流非主流、不言早到与新来、不论
发展程度高低,都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就是疆界内相互塑造并塑造国家的所有成员。这就
①
使得历史形态的民族在新的民族建构 ( nation building)中融洽起来,成为免除历史负担
① 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那些相对较好解决国家认同的国度,基本上都是尊重公民个人选择的国度。即使在这些国家
中存在集群冲突 (如法国)、族群矛盾 (如美国)、民族分裂 (如加拿大),也都可以诉诸制度手段加以解决,不
至于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暴力事件,甚至导致国家倾覆 (如南斯拉夫和苏联)。可见,现代国家的存续是一个很难
回避矛盾的艰难事宜,但只要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处理国家认同难题的方式方法。
前者,正是威尔·金里卡所指的政治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的第一种包容;后者则是他所指的自由民族主义对社群
主义的第二种包容。不在这两端之间达成平衡,国家认同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参见威尔·金里卡著 《当代政治哲
学》(下册),刘莘译,第六章第七节、第九节,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 418页以下、以及第 479页以下。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