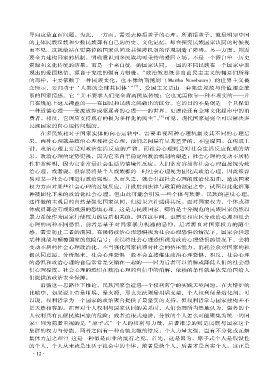Page 1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P. 14
导向应是直面问题。为此,一方面,需要去掉捂盖子的心理。所谓捂盖子,就是明知中国
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记忆,却在探究民族国家认同的时候视
而不见。这就给站在更高位的国家认同及其保障机制的浮现制造了障碍。另一方面,则需
要全力建构国家的机制,明确意识到多民族均可秉持的爱国立场,不是一个源自单一历史
资源和文化传统的结果,而是一个来自统一的国家认同。一国的不同民族在一个国家中表
现出的爱国热情,源自于宪法的强有力塑造。“政治效忠既非自由民主主义的拥趸们所称
的那样,主要依赖于一种民族文化,也不像纳斯鲍姆 ( Martha Nussbaum)的世界主义概
念所示,要归功于 ‘人类的全球共同体’” ,爱国主义是由一套宪法规范与价值理念维
〔 7〕
系的国家情感。它 “并不要求人们完全背离民族传统;它也无需依靠一种不现实的———并
且在规范上毫无裨益的———在国民和民族之间做出的区分。它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只保留
一种道德心理———受流放抑或驱逐者的心理———的世界,更遑论还有全球文化超市中的消
费者。相反,它理应支持现存的极为多样化的民主”。 可见,现代国家是完全可以解决多
〔 8〕
民族国家的向心运转问题的。
在多民族相对于国家实体的向心运转中,需要重视两种心理机制及其不同的心理后
果。两种心理就是政治心理和社会心理,他们之间是有显著差异的,不应混同。在构成上
讲,政治心理主要是对政治生活反应的产物,而社会心理则是对社会生活反应促成的结
果。政治心理的定势更强,因为它来自于稳定的政治机制的塑造;社会心理的变动不居特
性非常鲜明,因为它常常是社会生活的情境性反应。人们常常容易将社会心理直接视为政
治心理,或者说,很容易将某个人或族群的一时社会心理视为固化式政治心理,因此很容
易对某一社会心理进行政治强塑。久而久之,就会引起社会心理的政治化扭曲,造成国家
权力方面对某些社会心理的过敏反应,并投射到法律与政策的制定之中,试图以此化解那
种被固化下来的政治化社会心理。但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个体与族群、民族的逆反心理。
这样做的主观目的自然是强化国家认同,但结果兴许适得其反。面对国家权力,个体或群
体成员都会有或弱或强的恐惧心理,这是与民族国家、哪怕是十分规范的民族国家仍然以
暴力系统作为国家行使权力的后盾相关的。但在这中间,也需要相应区分政治心理和社会
心理的两种不同恐惧,前者是基于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忌惮,后者源自对国家权力的陌生
感,需要防止二者的混同。在误将政治心理恐惧视为社会心理恐惧的情况下,国家会轻忽
某种挑战与颠覆国家的危险信号;在误将社会心理恐惧视为政治心理恐惧的情况下,会将
变动不居的社会心理政治化,不当强化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挤压能力,消耗公众对国家的积
极认同意愿。分析起来,社会心理恐惧一般不会直接催生政治心理恐惧,相反,社会心理
的恐惧和政治心理的自信常常是交错在一起的———因为后者可以消解或降低人们的社会恐
惧心理程度。社会心理的恐惧在政治心理的自信中的消解,依赖的条件就是依宪治国给人
们提供的政治安全保障。
沿循这一思路往下推论,民族国家会遭遇一个权利哲学的实践天堑问题。在大熔炉的
比喻中,如果说上帝是坩埚、是火源,那么宪法则是坩埚支架,个人权利便是熔化剂。可
以说,权利哲学为一个国家的政治聚合提供了最坚实的支持。但权利哲学与国家建构并不
是天然相容的。在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强势的个
人权利具有瓦解民族国家的危险;或者追根式地讲,分散的个人怎么可能聚集为统一的国
家?因为前者重视的是 “原子式”个人的权利与力量,后者推崇的则是民族与国家这个
集群的权力与势能,两者之间有一种南辕北辙的悖反:个人力量太强,岂有不分化或瓦解
集体力量之理?!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流行之见。首先,这是因为,原子式个人是假设性
的个人,个人从来就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体。前者是伪个人,后者才是真实个人。这正是
2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