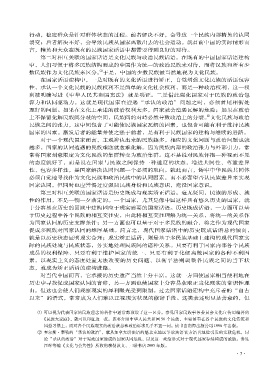Page 9 - 《党政研究》2023年第6期
P. 9
行动,稳定群众是针对群体状态的过程。前者解决不好,会导致一个民族内部精英的认同
裂变;后者解决不好,会导致民族从国家离散出去的社会运动。就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形而
言,精英和大众在既有的民族国家话语中都需要得到良好的对待。
第二对相互关联的国家话语是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话语。在既有的中国国家话语建构
中,人们习惯于将多民族结构而成的中国作为统一的政治民族来对待,而将汉族和所有少
数民族作为文化民族来区分。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被当然地视为文化民族。
①
在国家话语建构中,一是对既有的文化话语进行矫正,自觉增强文化民族的话语包容
性,承认一个文化民族的民族权利不是简单的文化社会权利,而是一种政治权利,这一权
利被明确写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明证。二是借此强化国家对于民族的政治包
容力和认同驱动力。这就是现代国家在遭遇 “承认的政治”问题之时,必须首尾相衔处
理好的问题。如果在文化上承诺的政治权利太多,国家就会遭遇瓦解的危险;如果在政治
上不保留化解民族间分歧的空间,民族间的对峙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裂。文化民族与政治
②
民族之间的张力,这中间包含了可能使民族国家瓦解的因素,也包含可能有利于维持民族
国家的因素。激发后者的能量并使之强于前者,是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建构与维续的进路。
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主观辨认出来的民族越多,相应的文化问题与政治问题也就
越多,国家的认同遭遇的民族难题就愈难化解。因为民族内部的政治张力与外部引力,常
常将国家刻意限定为文化民族的集群转变为政治集群。这不是说对民族怀抱一种视而不见
的态度就好了,而是说在国家与民族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状态,增进共同性、尊重差异
性、包容多样性,是国家解决认同问题一个必须的取向。就此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必须自觉地寻找作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中的认同因素,而不必奢望否认民族差异来实现
国家认同。但同时也应警惕过度强调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淹没国家意识。
第三对相互关联的国家话语是历史既成与现实矫正话语。毫无疑问,民族的形成、族
性的作用,不是一朝一夕落定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就
十分容易在历史的回顾中建构因应于现实需要的国家话语。历史既成话语,一方面可以基
于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的相互交往史,由此将相互交往理解为统一关系,将统一的关系作
为国家认同的历史支撑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基于对于多民族的融合,将之作为现代国家
促成多民族对国家认同的雄厚基础。简言之,现代国家话语中的历史既成话语总的倾向,
就是以历史状态证明现实合理;现实矫正话语,则是基于多民族基础上建构的现代国家实
际的民族处境与民族状态,务实地处理民族间的诸种关系。只要有利于国家内部各个民族
成员的权利保障、只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只要有利于化解离散国家的各种不利因
素,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处置无法改变的历史问题、以衡平法则调整各民族之间的当下状
态,就成为矫正话语的建构进路。
对当代中国而言,它承接的历史遗产当然十分丰富。这就一方面使国家相当便利地在
历史中寻找促成国家认同的言辞,另一方面也使国家十分容易获取正当化现实的常识性理
由。但这也会使人们观察现实的犀利眼光受到限制。过去国家话语建构中充斥着的 “自古
以来”的语式,常常成为人们难以正视现实状况的修辞手段。这类表述明显是善意的,但
① 可以视为代表国家的民族理念的著作中通常都预设了这一区分。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编著的
《民族大家庭》,就可以印证这一点。该书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 56 个民族,主要落墨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
风俗习惯上,而对各个民族现实的政治状态和政治诉求几乎不置一词。该书由南海出版公司 1996年出版。
② 查尔斯·泰勒的 “承认的政治”,就从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地区争取法语官方语言地位引发的宪政危机,讨
论 “承认的政治”对于宪政国家造成的国家认同危机,以及这一政治形式对于现代国家存续构成的威胁。参见
汪晖等编 《文化与公共性》所收的泰勒该文,三联书店 2005年版。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