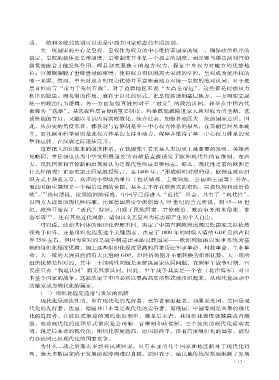Page 13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P. 13
质。一统和多统的区别可以说是中西方国家形态的本质区别。
大一统国家的中心是皇权,皇权作为权力的中心维持着国家的统一,确保政治秩序的
稳定。皇权的载体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制度,而是要与郡县制和官僚
制紧密配合才能发挥作用。郡县制克服独立的地方权力,保证中央权力对地方的优势地
位;官僚制摆脱了世卿世禄的束缚,使得权力得以脱离大家族的掌控,皇权成为统治权的
唯一来源。然而,中央对地方的权力优势并不意味着地方对统一皇权的绝对认同,对于底
层百姓而言 “帝力于我何有哉”,对于边疆地区来说 “天高皇帝远”,这些都是侵蚀权力
秩序的隐患。而礼制的作用,就在于以礼的形式,把皇权渗透到基层地方,一方面建立起
统一的政治行为逻辑,另一方面加强百姓的对于 “君父”的政治认同。科举在中国古代
被称为 “选举”,是选拔科层官僚的重要制度。科举既能破除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选
拔贤能的官员,又能以考试内容实现教化、统合社会,加强各地区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因
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郡县制与官僚制是单一中心权力体系的根基,在秦朝已经基本确
立,而礼制和科举制则是此权力体系的支持和动力,保障并维持了单一中心权力体系的完
整和运转,在汉唐之际逐步完善。
这套把人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在钱穆先生看来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英雄所
见略同,亨廷顿也认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贡献是直接诱发了欧洲现代性的官僚制。在西
方,民族国家和官僚制的出现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最重要标志。那么,现代性之前的欧洲是
什么样的呢?正如史家王国斌教授所言,在 1400 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
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 (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
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
统”。 换句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 “近代”社会,具有了 “现代性”。
〔 19〕
以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 19 世纪的兰克所说,到 15—16 世
纪,欧洲开始有了 “近代”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政治、政治事务的世俗化、常
备军等 ,还有其他近代现象,诸如以文艺复兴为标志而产生的个人自由。
〔 20〕
可以说,政治共同体的组织化程度不同,决定了中国直到欧洲出现民族国家之际依然
领先于世界。还是组织化程度这个关键因素,决定了 1800 年的时候大清的 GDP 虽然占世
界 25%左右,但因为面对的是战争制造出来的民族国家———欧洲列强的以军事系统为基
础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加上这些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国家历经军事革命、科技革命、工业革
命,大一统的大清虽然拥有大比重的 GDP,但经济数据并不能转换为组织优势。大一统的
组织优势是相对的,其中一个结构性问题是未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直到甲午战争时期,官
民还只有 “朝廷认同”而无国家认同。因此,甲午战争其实是一个省 (北洋海军)对日
本整个国家的战争。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以更高强度的形式被组织起来,从现代化运动中
的输家成为现代化的赢家。
(二)组织化程度递增与发展的陷阱
现代化是波次性的,即有现代化的先行者、竞争者和追赶者。如果说英国、美国是现
代化的先行者,法国、德国和日本等是现代化的竞争者,而俄国、中国等则是典型的现代
化的追赶者。在波浪式推进的现代化浪潮中,越是后来者,其组织化程度就越高或者越
强,驱动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依次是公司制、官僚制和政党制。三个波次的现代化运动表
明,越是后来者的现代化,组织化程度越高,原因很简单,没有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就没
有办法同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竞争。
为什么二战之后那么多新兴民族国家,只有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跻身于现代化行
列,绝大多数国家陷于发展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原因在于,殖民地传统深刻地限制了发展
1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