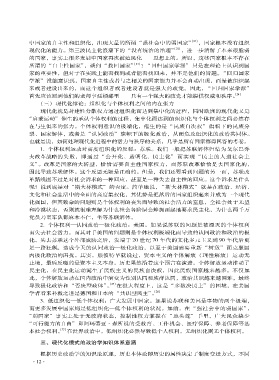Page 14 - 《党政研究》2023年第5期
P. 14
中国家的自主性和组织化,出现大量的所谓 “强社会中的弱国家” ,国家根本没有组织
〔 21〕
现代化的能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 “没有统治的治理” ,进一步消解了本来很脆弱
〔 22〕
的国家,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再次被殖民化———思想上的。所以,这些国家根本不存在
所谓的 “自主性国家”,谈何 “找回国家” ?“回归国家学派”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国
〔 23〕
家的重要性,但对于在实践上能否找到或者能否找回来,并不是他们的旨趣。“回归国家
学派”没能意识到,国家自主性或者与之相关的国家能力并不会自动出现,而是被组织起
来或者建设出来的,而这个组织者或者建设者就是强大的政党。因此,“回归国家学派”
首先应该回到他们的老师亨廷顿那里———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党才能提供权威和秩序。
〔 24〕
(三)现代化悖论:组织化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内在张力
现代化就是封建性分散权力通过组织化而达到集中化的过程,同时欧洲的现代化又是
“启蒙运动”催生的承认个体权利的过程,集中化而达到的组织化与个体权利之间必然存
在与生俱来的张力。个体权利意识的极端化,催生的是 “民族自决权”旗帜下的民族分
裂、国家解体,或者是 “认同政治”旗帜下的极化政治,从而危及组织化的政治共同体。
也就是说,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几乎是所有国家都得回答的考卷。
1. 个体权利运动对高度组织化的反弹:苏联。我们一般把苏联解体归结为戈尔巴乔
夫改革战略的失败,即通过 “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而实现 “民主的人道社会主
义”。改革是国家的大转型,恰恰需要自主性国家权力,而苏联改革恰恰是去国家化的,
因此导致苏联解体。这个反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苏联改
革路线图不过是对社会诉求的一种回应,甚至是一种失去自主性的回应。这个诉求是什么
呢?说到底是对 “斯大林模式”的否定。简单地说,“斯大林模式”就是在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的高度集权化,其优势是把落后的国家组织起来并成为一个现代
化强国,但其致命的问题则是个体权利的丧失而导致的社会活力的窒息,全社会处于无望
和冷漠状态,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社会各阶层会蜂拥而起地要求民主化,为什么两千万
党员乃至军队都麻木不仁,坐等苏联解体。
2. 个体权利—认同政治—极化政治:美国。如果说苏联的问题是被湮灭的个体权利
而失去社会活力,而其对手美国的问题则是个体权利极端化而导致的认同政治和政治的极
化。失去苏联这个外部威胁之后,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到 90 年代后更
是一路狂飙,造成今天的认同政治—极化政治,以至于美国需要重新 “树敌”而克服国
内极化政治的困扰。其实,熊彼特早就说过,资本主义的个体解放 (理性解放)运动无
止境,最后反噬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历史果然沿着这个预言在演进。个体解放运动推动了
民主化,在民主化运动诞生了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决权,因此民族国家越来越多。不仅如
此,个体解放运动在国内政治中演变为性别认同和族群认同,政治共识越来越困难,最终
导致极化政治和 “否决型政体”。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 “多数决民主”的困境,在美国
〔 25〕
学者看来补救之道是德国和日本的 “共识型民主”。
〔 26〕
3. 低组织化—低个体权利:广大发展中国家。如果说苏联和美国是事物的两个极端,
而更多发展中国家则是低组织化—低个体权利的状况。如前,在 “强社会中的弱国家”,
“弱国家”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控制性权力掌握在 “地头蛇”手里,广大民众缺少
“可行能力的自由”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受教育、工作机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基
本社会权利。 在世界政治中,低组织化必然导致低个人权利,无组织化则无个体权利。
〔 27〕
三、现代化模式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意涵
根据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论原理,历史本体论即历史的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不同
2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