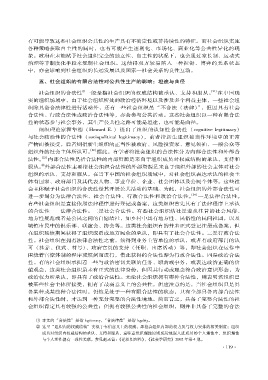Page 121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121
有可能导致这些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产具有不确定性或非持续性的特征。而社会组织实施
各种策略获取自主性的同时,也有可能产生逐利化、市场化、商业化等公共性异化的现
象。政府在未能赋予社会组织完全的独立性、自主性的状况下,也会通过家长制、运动式
治理等非制度化手段来规制社会组织。这使得双方较易陷入一种拉锯、博弈的关系状态
中,亦会影响到社会组织的长远发展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五、社会组织的有限合法性对公共性生产的影响:坦途与曲径
社会组织的合法性 一般是指社会组织的权威结构被承认、支持和服从。 在中国现
〔 21〕
①
实的组织场域中,由于社会组织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涉及多个利益主体,一些社会组
织除具备合法律性进行活动外,还有一些社会组织虽 “不合法 (法律)”,但因具有社会
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等,亦会参与公共活动。这些社会组织以一种有限合法
性的状态参与社会事务,其生产公共性之路可能是坦途,也可能是曲径。
组织理论家霍华德 ( Howard E.)提出了组织的认知性合法性 ( cognitive legitimacy)
与社会政治性的合法性 ( sociopolitical legitimacy),前者指新生组织被当作环境中的正常
产物而被接受,后者则指新生组织的正当性被政府、风险投资家、意见领袖、一般公众等
组织外的社会主体所认可。 据此,有学者将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
〔 22〕
法性。 内部合法性是指合法性的内部资源是来自于组织成员对权威结构的承认、支持和
〔 23〕
服从。外部合法性主要指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外部资源是来自于组织外部的社会主体对社会
②
组织的承认、支持和服从。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场域中,对社会组织表达承认的社会主
体有国家、政府部门及其代表人物、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体等。这些社
会主体赋予社会组织的合法性是其开展公共活动的基础。为此,社会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可
进一步划分为法律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 一是法律合法性。
〔 24〕
有些社会组织是直接依照法律程序进行登记或备案,这类组织首先具有了法律程序上承认
的合法性———法律合法性。二是社会合法性。有些社会组织结社是遵从往昔的社会风俗、
地方性规范或者是公民之间的自愿结社,如乡村中具有地方性、民俗性的民间社团,以及
城镇市民中的俱乐部、联谊会、协会等。这类社会组织有的并未正式登记注册或备案,但
在组织延续期间获得了组织成员或地方民众的承认,即具有了社会合法性。三是行政合法
性。社会组织在拥有法律合法性之前,须得到业务主管单位的承认,或者有政府部门的认
可 (挂靠、仪式、符号)、政府官员的支持 (任职、出席活动)等,即社会组织在运作中
围绕着官僚体制的程序或惯例而进行,借此获得的合法性即为行政合法性。四是政治合法
性。有的社会组织承担着一些与政治密切关联的任务、职责或事务,或表达政治正确的价
值观念,这类社会组织虽未有正式的法律身份,但因其行动或理念符合政治意识形态,为
政治权力所承认,即具有了政治合法性。无论社会组织拥有哪种合法性,则表明该组织已
被某些社会主体所接受,拥有了最弱意义上的公共性。但应注意的是,当社会组织只是具
备某种或某些种合法性时,仍然是处于一种有限合法性的状态,只有全部具备内部合法性
和外部合法性时,才达到一种充分完整的合法性境地。简而言之,具备了完整合法性的社
会组织肯定具有较强的公共性;但拥有较强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则并非具备了完整的合法
① 本文的 “合法性”是指 legitimacy,“合法律性”是指 legality。
② 这里 “组织内的权威结构”类似于韦伯意义上的权威,即社会组织内部的权力及与权力安排的相关制度;组织
成员对组织内权威结构的承认、支持和服从,意味着组织理性原则成功地嵌入进成员的个人理性中,组织理性
与个人理性拥有一致性关联。参见赵孟营:《论组织理性》,《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 4期。
1 · ·
1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