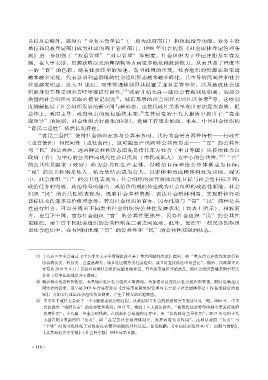Page 11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4期
P. 118
员以及章程外,还须有 “业务主管单位”(一般为政府部门)担负起指导功能。业务主管
单位和民政登记部门成为社团的两个管理部门。1998 年出台的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进一步加强了 “双重管理” “对口管理”等制度。社会组织为了登记注册及生存发
展,在人事安排、资源获取以及治理结构等方面更多地依赖政治权力,从而具备了程度不
一的 “官”的色彩。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新型社团的出现,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渠道
越来越多元化,代表新型利益群体的社会组织形态越来越多样化,其本身的民间性和社会
性也越发明显。进入 21 世纪,双重管理体制因其设置了业务主管单位,以及造成社会组
织的身份差异受到多方呼吁要进行调整。 政府开始允许一些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如部分
〔 15〕
类型的社会组织可采取直接登记制度 ,城市基层的社会组织可到社区备案 等。这些制
①
②
度创新拓展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空间与新形态,也使得政社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态势,但
总体上,政府主导、政府负责的地位始终未变。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 “党全
③
面领导”的原则,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的同时,党建工作逐步加强。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
“官民二重性”依然长期存在。
“官民二重性”使得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其行为会带有两种特性———行政性
(或官僚性)和民间性 (或社会性),这可能生产出两种公共性形态——— “官”的公共性
与 “民”的公共性。这两种公共性形态原先是指代东方社会 (中日等国)从传统社会以
政府 (官)为中心的公共性向现代社会以民间 (市民或私人)为中心的公共性。 “官”
〔 16〕
的公共性是国家 (政府)作为公共性生产主体,以政治目标和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
“民”的公共性则是私人、私力集结而成为公共,以群体利益或团体利益为目标。现实
中,社会组织 “官”的公共性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宗旨将政治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并列;
政治任务的完成、政治符号的输出、政治价值观的传递成为社会组织的政治性职能。社会
组织 “民”的公共性则表现为,汲取社会多种资源、表达社会群体利益、实现群体行动
目标以及传递多元价值理念等。若以社会组织的官办、民办性质与 “官”“民”两种公共
性进行组合,可以分离出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发展状况 (如表 1 所示)。相较而
言,在当下中国,官办社会组织 “官”的公共性更强些,民办社会组织 “民”的公共性
更强些,而半官半民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则在二者之间流动。此外,近些年一些民办的枢纽
型社会组织中,亦有同时出现 “官”的公共性和 “民”的公共性双强的状态。
①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
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随后,民政部正式
宣布从 2014年 4月 1日起对四类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有些省市地区开始试点,但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中有关
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并未修改。
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不断涌现。为加强对这些社区社会组织的管理,同时也满足民
间结社的需求,最早是 2003年青岛市发布 《青岛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关于建立社会团体登记工作备案制度的通
知》,开始实行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制度,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
③ 中央对于政社关系处于一个不断探索认知的过程,从政府对于社会的职责的官方表述可见一斑。2004年,中央
首次提出 “政府负责”的社会管理格局;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中要发挥政府
负责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强调,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2017 年党的十九
大报告则又重新回归 “负责”,即 “在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中,发挥政府负责作用”。这种从政府 “负责”与
“主导”间的变化体现了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理性反思。参见陈鹏:《中国社会治理 40 年:回顾与前瞻》,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6期。
1 · ·
1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