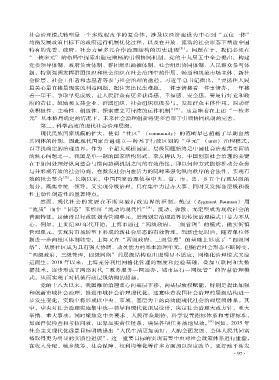Page 99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P. 99
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一个多线程改革的复合体,涉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 “五位一体”
均衡发展政策目标下的政府运行机制优化过程,以及在开放、流动的社会形态下塑造中国
特有的党委、政府、社会力量多元合作治理结构的历史进程 。问题在于,我们必须在
〔 31〕
“一核多元”的格局中探索出稳定顺畅的引领协同机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
党委领导体制、政府负责体制、群团组织助推体制、社会组织协同体制、人民群众参与体
制,特别强调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
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
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履行好党和政
府的责任,鼓励和支持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发挥群众主体作用,调动群
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建立可持续的运作机制” 。这意味着在上述 “一核多
〔 32〕
元”基本格局确定的情况下,未来社会治理创新将更多着眼于引领协同机制的完善。
第二,科学高效的现代社会治理层级。
现代民族国家规模的扩大,使得 “社区” ( community)的范畴早已超越了早期自然
共同体的时期。因此现代国家普遍建立一种基于行政区划的 “单元” ( unit)治理模式,
以寻找确定的治理边界。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层级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治理需要面临
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李友梅认为,中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
在于如何处理好纵向整合与横向协调机制之间的有效衔接,即以何种方式能够推动公众参
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在激发社会内在活力的同时来强化纵向秩序的合法性,实现有
效的社会整合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依靠中央、省、市、县、乡五个行政层级的
〔 33〕
划分,既集中统一领导,又实现分级治理,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又发挥各层级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显著特点。
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突破行政边界的框制。鲍曼 ( Zygmunt Bauman)用
“流质”而非 “固态”来形容 “流动的现代性” ,流动、弥散、无定型成为现代社会的
〔 34〕
普遍特征。这使得以行政区划为管理单元,进而划定治理边界的传统治理模式日益力不从
心。例如,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上海市通过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做实街镇
管理单元,实现对市场转型下形成的新社会形态的有效管理。到新世纪以后,随着单位体
制进一步向社区体制转变,上海又在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基础上形成了 “四级网
络”,基层社区成为具有强大协调、动员能力的基本治理单元。但随着社会形态不断转变,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层级结构也出现明显不适应,网格化治理模式又应
运而生。2018 年以来,上海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和经验基础,叠加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逐步形成了网络时代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的智慧治理模
式,从而实现了对机械行政层级结构的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向基层放权赋能,特别是提出加强
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意味着我国社会治理的层级结构进一
步发生变化,实践中将形成以中央、市域、基层为主的高效能现代社会治理层级体系。其
中,中央对社会治理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和现代化顶层设计,决定社会治理大政方针、重大
举措、重大事项。同时聚焦党中央要求、人民群众期待,科学设置指标体系和考评标准,
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问效,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例如,2035 年
〔 35〕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明确提出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重要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央对社会政策体系进行重塑,
在收入分配、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权利均等化等许多方面加以深度改革,更好地平衡发
7 ·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