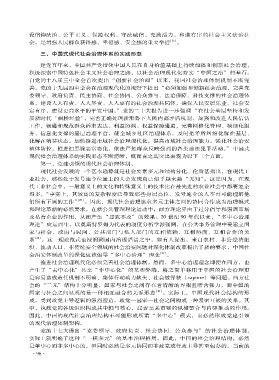Page 98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P. 98
设信仰法治、公平正义、保障权利、守法诚信、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
会,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
〔 26〕
三、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践形态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自身价值基础上持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 “中国之治”的基石。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 “创新社会治理”以来,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下提出 “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
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
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
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社会治安
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式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践形态不断清晰,概而言之其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党建引领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社会要素多元和结构分化。伦斯基指出,在现代工
业社会,那些处于发号施令位置上的人会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 “无知”。这是因为,在现
代工业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技术比在最先进的农业社会中都要复杂
得多,“事实上,其较高的复杂程度已导致那些身居高位、发号施令的人不再可能理解他
们所有下属的工作” 。因此,现代社会治理追求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成为治理模式
〔 27〕
和理论革新的必然要求。在新公共管理理论运动中,西方理论界由于过分倡导和强调市场
及私营企业的作用,从而产生 “过犹不及”的效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多中心治理
理论”应运而生,以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强调,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要建立国
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互相依赖、互相协商、互相合作的关
系 。这一理论范式也浸润到国内治理话语之中,如有人提出,来自农村、非公经济组
〔 28〕
织、流动人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社会治安问题对深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社
会治安体制改革的深化应该倡导 “多中心治理”理念 。
〔 29〕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然而,多中心治理理念即便在西方,也
产生了 “去中心化”甚至 “非中心化”的某些弊端,将之简单移用于中国的社会治理更
是容易造成责任机制不明确、集体行动动力缺失、社会被俘获 ( capture)等问题。西方社
会的 “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且暗含张力,而中国的
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现的是一种相互融合的关系形态 。实际上,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形
〔 30〕
成,受到政党主导逻辑的强烈塑造,政党—国家—社会之间构成一种紧密互嵌的关系。其
中,执政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其中轴与核心,起着至关重要的纵横整合与内驱推动的作用。
因此,中国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不可能形成所谓 “多中心”模式,而必然形成党建引领
的现代治理体制架构。
党的十七大提出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
实际上就明确了这种 “一核多元”的基本治理格局。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结构,必然
是单中心而非多中心的,但同时必然是多元协同而非政党或行政主导甚至包办的。当前的
6 · ·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