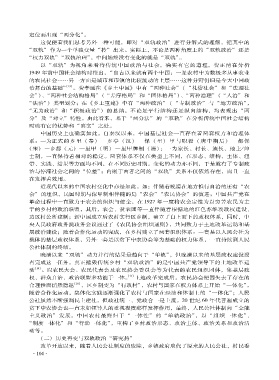Page 106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P. 106
定位而出现 “两分化”。
这促使着我们思考另外一种可能,即对 “双轨政治”进行分解式的理解,把其中的
“双轨”作为一个单独变量 “拎”出来。实际上,不论是两种角度上的 “双轨政治”还是
“权力双轨”“双轨治理”,中间始终没有变化的就是 “双轨”。
以 “双轨”为视角来看待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确实有它的道理。费正清在分析
1949 年前中国社会结构时指出,“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中为数极多从事农业
的农民社会……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
治舞台的基础”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有 “两种社会”(“礼俗社会”和 “法理社
〔 13〕
会”)、“两种社会结构格局”(“差序格局”和 “团体格局”)、“两种治理”(“人治”和
“法治”)类型划分;在 《乡土重建》中有 “两种政治”(“专制政治”与 “地方政治”,
“无为政治”和 “积极政治”)的总结。不论是平行结构还是纵向结构,均表现出 “两
分”及 “对立”特性。由此看来,基于 “两分法”的 “双轨”在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
时确有它的优势和 “真实”之处。
中国历史上也确实如此。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社会一直存在着两套权力和治理体
系:一为正式的乡里 (秦) !乡亭 (汉) !保 (里)甲与职役 (唐中期后) !都保
(宋)!乡都 (元)—里甲 (明)!里甲牌制 (清);一为家长、村长、族长、地主 /绅
士制,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两套体系不仅在类型上不同,在形态、结构、主体、纽
带、实践、结果等方面均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的动力亦不同,于是就有了专制政
治与停滞社会之间的 “位差”;内嵌于两者之间的 “双轨”关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一直
在发挥着效用。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农村变化中亦是如此。如:伴随着晚清在地方推行自治的还有 “农
会”的组织,民国时期与保甲制相伴随的是 “农会”“农民协会”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在
革命过程中一直致力于农会的组织与健全,在 1927 年一度将农会定性为以穷苦农民为主
干的乡村的政治联盟,其后,农会、贫农团等一直伴随着根据地的红色苏维埃政权建设、
边区村公所建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实行区乡制,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政权体系,同时,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了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共同致力于土地改革运动和基
层政治建设;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完成,在乡村建立了两套组织体系:一套是以人民公社为
载体的基层政权体系,另外一套是以贫下中农协会等为基础的权力体系,一直持续到人民
公社体制的终结。
晚清以来 “双轨”动力并行的结果是趋向于 “单轨”,但晚清以来的基层政权建设没
有完成这一任务。真正摧毁传统乡村 “双轨政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
动 。以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农民协会委员会等为代表的农民组织团体,集基层政
〔 14〕
权、群众自治、政治联盟多功能于一体。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协会便因失去了存在的
〔 15〕
合理性而悄然隐退 ,区乡制变为 “行政村”,农村与国家在权力体系上开始 “一体化”。
〔 16〕
随着合作化运动,集体化实践逐渐强化了农村与国家在经济和体制上的 “一体化”;人民
公社虽然不断强调民主建社,但政社统一、党政合一是主流。20 世纪 60 年代普遍成立的
贫下中农协会也一直未如领导人的重视程度那样发挥作用,最终,人民公社体制向 “全能
主义政治”发展。中国农村最终归于 “一体性”的 “单轨政治”,以 “组织一体化”、
“制度一体化”和 “行动一体化”,重构了乡村政治形态、政治主体、政治关系和政治活
动等。
(二)历史再变与双轨政治 “研究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乡镇政府取代了原来的人民公社,村民委
0 · ·
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