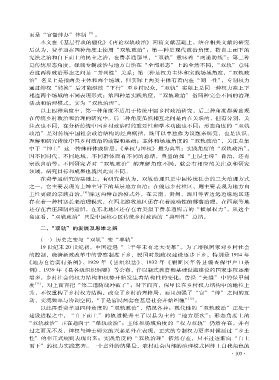Page 105 - 《党政研究》2023年第3期
P. 105
而是 “官督绅办”体制 。
〔 9〕
本文在 《基层行政的僵化》《再论双轨政治》两篇文献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
后认为,费孝通在四种角度上使用 “双轨政治”:第一种是现代政治角度,指自上而下的
宪法之治和自下而上的民主之治,在费孝通那里,“双轨”意味着 “两道防线”;第二种
是传统形态角度,强调专制政治与地方自治在 “全部形态”上的全然不同,“双轨”意味
着这两种政治形态之间是 “并列性”关系;第三种是权力主体和实践场域角度,“双轨政
治”名义上是指两类主体和两个场域,但实际上两类主体有着内在 “同一性”,专制权力
通过绅权 “转换”后才能继续 “下行”至乡村民众,“双轨”实际上是同一种权力在上下
相连两个场域的不同表现形式;第四种是实践角度,“双轨政治”指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
活动和治理模式,实为 “双轨治理”。
以上四种角度中,第一种角度不适用于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后三种角度都曾出现
在传统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研究中。后三种角度虽然相互之间是内在关联的,但有分别,关
注点也不同,在分析传统中国乡村政治时的重要性和学术功能也不同:形态角度的 “双轨
政治”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经典概括,既可以单独作为议题来研究,也是认识、
理解和研究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主体和场域角度的 “双轨政治”,关注点集
中于 “绅士”这一特殊群体或阶层,《皇权与绅权》最为典型;实践角度的 “双轨政治”,
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群体而有不同的总结,典型的如 “上层士绅”自治,还有
宗族自治等。不同研究者对 “双轨政治”的理解角度不同,就会有相应的关注点和研究
领域,研究目标和成果也就因此而不同。
在费孝通研究的基础上,有研究者认为,双轨治理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治理方式
之一,它主要表现为士绅主导下的基层地方自治;在偏远乡村社区,则主要表现为地方自
主性更强的宗族自治。 除这两种自治模式外,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边远边缘地区还
〔 10〕
存在着一种村寨长老治理模式,在西北游牧地区还存在着流动性的部落治理,在西藏等地
还存在着庄园制的遗留,在东北地区还存在着类似于费孝通所言的 “横暴权力”。从这个
角度看,“双轨政治”只是中国核心区传统乡村政治的 “典型性”总结。
二、“双轨”的发展及思维之辨
(一)历史之变与 “双轨”变 “单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为了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
的控制,晚清新政改革中的警察制度下乡,民国时期政权建设逐步下乡,特别是 1914 年
《地方自治实行条例》、1929 年 《县组织法》、1932 年 《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
例》、1939 年 《县各级组织纲要》等公布,伴以新式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事权逐渐
增多,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势开始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曾经 “夹缝”中的保甲制
度 ,对上而言把 “第二道防线冲破了”;对下而言,保甲长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上
〔 11〕
升,不仅重构了乡村权力结构,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而且加强了 “官”“绅”之间的互
动、交流频率与协调空间,“于是官民两套在基层社会开始纠缠” 。
〔 12〕
以此再看费孝通四种角度的 “双轨政治”,情况各异:现代性的 “双轨政治”正处于
建设进程之中, “自下而上”的轨道提升至了以县为主的 “地方层次”;形态角度上的
“双轨政治”正在趋向于 “单轨政治”;主体和场域角度的 “权力双轨”仍然存在,并有
过之而无不及,绅权与绅士研究的兴起是外在表现,正式的专制权力更多时候通过 “乡土
性”的非正式规则表现出来;实践角度的 “双轨治理”依然存在,只不过逐渐向 “自上
而下”的权力实践靠齐。一个意外的结果是,农村社会内部的治理模式因绅士自我角色的
0 · ·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