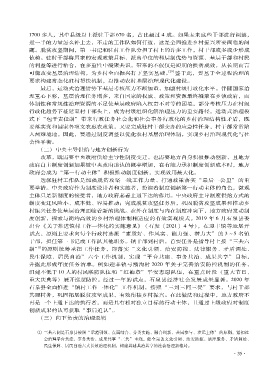Page 36 - 《党政研究》2021年第6期
P. 36
1700 多人,其中县级以上派驻干部 670 名,占比超过 4 成。如果未来这些干部进行调整,
近一半的力量怎么补上去,不走的工作队如何打造,这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要面临的问
题。脱贫攻坚期间,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分担了村上的许多工作,村干部或多或少形成
依赖。驻村干部将国家的宏观政策目标、派出单位的科层制优势与资源、基层干部和村民
的利益等进行粘合,在多重性中凝聚共识,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的扶贫成效,从长期而言
可能改变基层治理结构,为乡村全面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鉴于此,要基于全过程治理的
〔 29〕
要求构建常态化驻村帮扶机制,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
最后,运动式治理情势下基层考核压力不断加重,加剧村级行政化水平。伴随国家治
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来自国家的权威、政策和资源最终凝聚在乡镇政府,而
体制性和常规性治理资源的不足使基层政府陷入权责不对等的困境,部分考核压力在村级
行政化趋势下蔓延至村干部头上,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路径。运动式治理模
式下 “包干责任制”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既
要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又要完成驻村干部交办的应急性任务,村干部常常陷
入两难境地。因此,要通过制度调整以优化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与社
会性平衡。
(二)中央主导供给与地方创新行为
改革,既需要中央政府供给主导性制度变迁,也需要地方自身积极推动创新,且地方
政府自主制度创新如果被中央政府追认的概率增加,在有能力承担制度创新成本时,地方
政府会成为 “第一行动主体”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实现效用最大化。
选派驻村工作队是加强脱贫攻坚一线工作力量、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的重
要举措。中央政府作为制度设计者和实施者,扮演着制度创新第一行动主体的角色,微观
主体只是新制度的接受者,地方政府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中央政府主导制度供给方式的
制度变迁风险小、成本低、容易推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
村振兴任务使基层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冲突下,地方政府发动制
度创新,探索与简约高效的乡村治理体制相适应的有效实现模式。2019 年 6 月石泉县委
出台 《关于推进镇村工作一体化的实施意见》 (石发 〔 2021〕4 号),在迎丰镇等地展开
试点,原则上要求向每个行政村选派 “素质好、作风实、能力强、潜力大”的 3 ~ 5 名镇
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其他职务。镇干部到村后,首要任务是指导村上按 “三共六
制”的原则统筹承担工作任务,即落实 “文化引领、治安防控、法律服务、矛盾调处、
①
民生保障、居民自治”六个工作机制,实现 “平台共建、事务共治、成果共享”目标,
并据此形成年度任务清单。例如迎丰镇弓箭沟村 2020 年关于完善治安防控机制的任务,
组建不低于 10 人的村民联防队伍和 “红袖章”平安志愿队伍,在重点时段 (重大节日、
重大庆典等)展开巡逻防控。经过一年的试点,石泉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显著。2020 年
石泉县全面推进 “镇村工作一体化”工作机制,按照 “三到三同三促”要求,与村干部
共理村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在此做法和过程中,地方政府不
再是一个上通下达的执行者,而是具有相对独立目标的行动主体,且通过上级政府对制度
创新成果的认可获取 “事后追认”。
(三)向下负责的治理逻辑
① 三共六制是石泉县按照 “示范引领、点面结合、分类实施、融合创新、共同参与、多元主体”的原则,紧扣社
会治理平台共建、事务共治、成果共享 “三共”主线,健全完善文化引领、治安防控、法律服务、矛盾调处、
民生保障、居民自治六大长效治理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5 ·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