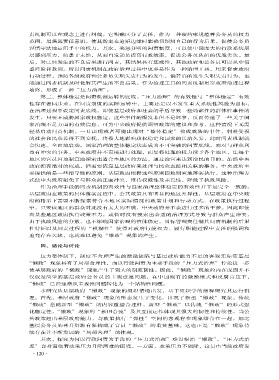Page 110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P. 110
责机制可以在观念上进行纠偏,它明确区分了责任,作为一种硬约束规范着公务员的权力
范围,增强其责任意识,使其游走在逾矩边缘时能确切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促使公务员
谨慎守法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其次,奖惩分明的问责制度,可以使中国庞大的行政系统层
层感到压力,防患于未然,从而自发动员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公务员队伍的优胜劣汰。最
后,对已经发生的不良后果进行问责,其结果具有惩戒性,其他政府和公务员可以从中借
鉴经验和教训。所以问责机制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更多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用来督责政府
行动过程,预防各级政府和公务员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倘若真的发生失职失责行为,也
能通过问责机制及时化解其产生的不良后果。作为治理工具的问责机制贯穿政府治理过程
始终,形成了一种 “压力治理”。
第二,整体稳定是问责机制运转的底线。“压力治理”的有效性与 “整体稳定”有效
性存在着同步差。在问责制度的实际运转中,主要还是以不发生重大系统性风险为目标,
在治理过程中设定问责底线。即使基层政府和社会的矛盾导致一些局部性的群体性事件的
发生,只要不威胁国家政权稳定,这些事件的爆发非但不是坏事,反而传递了一些关于国
家治理不足方面的有效信息,可为中央政府提供调整政策的建议和参考,这种情况下无需
轻易启动问责机制。一旦出现或者可能出现对 “整体稳定”构成威胁的事件,利益受损
的社会和民众若得不到安抚,将极大地影响政权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此时问责机制就
会快速、全面地启动。国家治理的整体稳定状态成为不可突破的问责底线。面对与群众利
益有冲突的事务,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进行处理,而是将处理的权力授予各个地区,让每个
地区的官员因地制宜地探索出适合本地区的方法,通过治官来达到治民的目的。虽然中央
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威,但需要依靠基层政府来处理与民众直接相关联的事务。中央政府主
要提供的是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基层政府根据这些原则因地制宜地落实执行。这种治理方
式使中央政府避免了与群众的正面冲突,维持权威性及亲民性,降低了执政风险。
作为治理手段的问责机制的有效性与国家治理整体稳定的有效性并非是完全一致的。
基层政府在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中,公共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基层政府在中央政
府的指示下需要不断探索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计划和行动方式。在政策执行过程
中,只要该地区的群众对此没有太大的不满,中央政府并不会进行过多的干涉。因此即使
有某些地区政府执行政策不力,或暂时没有摸索出合适的治理方式导致与群众产生冲突,
由于执政风险的分散,也不影响国家治理的整体稳定。目标管理责任制其问责机制的后果
性特征以及问责过程的 “模糊性”使得对政府行使权力、履行职能过程中责任的强调和
追究存在欠缺,也就难以避免 “懒政”现象的产生。
四、结论与讨论
压力型体制下,制度不合理产生的激励缺陷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客观实际使基层
“懒政”现象具有了局部合理性,而以行政问责为主要手段的 “压力式治理”悖论进一步
使基层政府的 “懒政”现象产生了强大的制度韧性。因此,“懒政”现象的内在成因并不
仅仅是简单的基层政府公务员的主观意愿问题,在中国现有的激励模式和反腐高压下,
“懒政”已经逐渐从主观性问题转化为一个结构性问题。
本研究从基层政府 “懒政”现象的组织情境出发,基于组织学的解释研究其运行机
理。首先,基层政府 “懒政”现象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型 “懒政”现象。传统
“懒政”借助新型 “懒政”的内容重塑合理性,新型 “懒政”以传统 “懒政”的形式强
化稳定性,“懒政”现象的 “新旧合流”及其互嵌运作体现其强大的韧性和持续性。当公
共政策超出基层政府能力,与政策执行 “弹性”空间的客观存在现象结合在一起,加之
基层公务员的晋升资源有限构成了官员 “懒政”的重要基础。这也正是 “懒政”现象持
续存在并不断发展的 “局部合理”的体现。
其次,探究为何以行政问责为手段的 “压力式治理”难以根治 “懒政”。“压力式治
理”自身面临着政策压力升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政策压力不能降,这是由当前政府发
2 · ·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