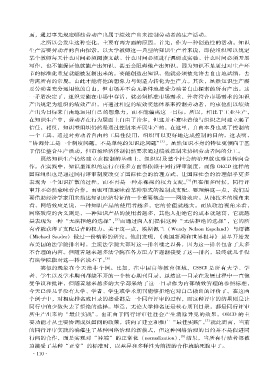Page 100 - 《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P. 100
面,通过事先规定哪些劳动产出属于绩效产出来控制劳动者的生产活动。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知识
生产需要劳动者的自由探索。以大学教师这一典型的知识生产者来说,即使组织可以规定
某个教师每天什么时间必须阅读文献、什么时间必须进行调研或实验、什么时间必须开展
写作,也不能保证他就能产出知识,甚至会阻碍他产出知识,因为知识不是通过对生产环
节的标准化重复就能被复制出来的。要能创造出知识,他就必须被允许去自由地试错,去
背离所有的常规,由此才能将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转化为生产力。其次,虽然知识生产需
要劳动者充分运用他的自由,但市场并不会无条件地接受劳动者自由探索的所有产出。这
一矛盾决定了,组织要能在市场中存活,就必须抓准市场需求,并将符合市场需求的知识
产出规定为组织的绩效产出,再通过相应的绩效奖惩体系来控制劳动者,约束他们以绩效
产出为目标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而不能偏离这一目标。所以,相比于工业生产,
在知识生产中,劳动者在行为层面上自由了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组织之间建立起了
信任,相反,知识型组织仍然是通过控制来开展生产的,在这里,自由本身也成了控制的
一个工具,通过对劳动者自由的工具性使用,组织可以更好地达成控制的目的。这表明,
“协调分工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单纯的知识论问题” 。虽然知识本身的特征更倾向于基
〔 3〕
于信任整合生产活动,但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求通过绩效控制来协调劳动者间的分工。
既然知识生产仍然建立在控制的基础上,组织以及整个社会的治理就也难以转向合
作。在实践中,知识型组织的运行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同行评审制度,而像 OECD 这样的
国际组织也是通过同行评审制度改变了国际社会的治理方式,让国际社会的治理似乎更多
表现为一个知识扩散的过程,而不再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支配。 但在很多时候,同行评
〔 4〕
审并不必然意味着合作,而也可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控制或支配。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
要借助经济学家用来描述知识经济特征的一个重要概念———网络效应。从纯技术的视角来
看,网络效应是说,一种知识产品的使用者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而从政治视角来看,
网络效应的含义则是,一种知识产品的使用者越多,其他人拒绝它的成本就越高,它就越
是表现为一种 “无法拒绝的选择”, 而通过向人们提供这种 “无法拒绝的选择”,它的所
〔 5〕
有者就获得了支配后者的权力。关于这一点,埃斯佩兰 ( Wendy Nelson Espeland)与绍德
( Michael Sauder)做过一份精彩的研究。他们发现,《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最早开始发
布美国的法学院排名时,主流法学院大都对这一排名嗤之以鼻,因为这一排名包含了太多
不合理的内容。但随着越来越多法学院在各方压力下逐渐接受了这一排名,最终就几乎没
有法学院能对这一排名说不了。
〔 6〕
类似的现象在今天绝非个例。比如,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CSSCI 是所有大学、学
者、学生以及学术期刊都绕不开的一个核心期刊目录,虽然这一目录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饱
受争议和批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都采纳了这一目录作为内部绩效管理的参照标准,
今天已经几乎没有大学、学者、学生或学术期刊能够拒绝它对自己做出的评价了。在这两
个例子中,对相应排名或目录的接受都是一个同行评审的过程,而这种评审的结果则是让
同行中的少数失去了拒绝的选择。毕竟,无论大学排名还是核心期刊目录,都是同行评审
所生产出来的 “最佳实践”。也正由于同行评审往往会产生消除异见的效果,OECD 的主
要功能才从主要协调成员国间的政策,转向了建立和推广 “最佳实践”。 就此而言,当前
〔 7〕
的同行评审实践的确催生了某种网络治理的新模式,但这种网络治理的目的并不是促进同
行间的合作,而是实现对 “异端”的正常化 ( normalization), 结果,当所有行动者都被
〔 8〕
迫接受了某种 “正常”的标准时,以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的合作就胎死腹中了。
1 · ·
1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