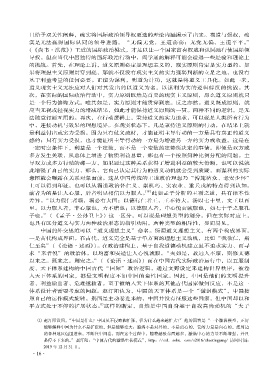Page 17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P. 17
且给予双关性阐释,确实将国际政治领导权更迭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出来。霸道与强权,确
实是无法赢得国际认同的领导进路。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尚书·洪范》)王道的国际政治模式,才足以让一个国家富有权威和认同地行使国际领
导权。但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国际政治行动中,阎学通的解释可能会遭遇一些经验和理论上
的挑战。首先,在理论上讲,道义原则必定是理想主义的,现实原则肯定是实力型的。如
果将理想主义原则贯穿到底,那就不仅没有现实主义的实力强弱判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
基于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谊为谋利,明道为计功,这就是将道义工具化。如此一来,
道义现实主义无法应对人们对其发出的以道义为名,以谋利为实的逻辑悖反的挑战。其
次,在实际的国际政治行动中,实力原则既然是首要的现实主义原则,那么道义原则就只
是一个行为修饰方式。唯其如是,实力原则才能贯穿到底。反之亦然。道义既成原则,就
应当无视或轻视实力的增减结果,如此才能保持道义原则的一贯。两种不同的逻辑,是无
法随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动逻辑上,秉持道义的实力追求,可以说是人类所有行为
中,连接动机与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现实状态下,凡是秉持道义原则的行动,在结果上就
是利益付出或实力受损。因为只有仗义疏财,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义
感的;只有实力受损,也才能证明主导行动的一方是为增进另一方的实力或收益。这是在
一定时空条件下,利益是一个定数,而不是一个变数的定势所决定的事情。即便是双方或
多方发生关联,从总体上增进了物质利益总量,那也有一个按照何种比例分配的问题。主
导双方或多方行动的那一方,如果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增进利益的较大份额,也可以说就
此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那么,它自己认定其行为的道义动机就会受到质疑,而谋利的实际
意图就会曝露在关系对象面前。这从中国传统的王道政治理想乃 “博施济众、老安少怀”
上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霸道政治怀仁义、崇机巧、实农业、重兵戎的特点得到认知。
前者为的是让人心服,后者明显相信以力服人。 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
〔 18〕
差异。“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
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一区分,可以说是理想类型的划分。但在实际对应上,
也具有区分道义与实力两种政治形态的指引功用。两种类型的相斥性,显而易见。
中国的外交思维可以 “道义理想主义”命名。所谓道义理想主义,有两个构成界面。
一是古代构成界面。在古代,道义完全是基于单方面的理想主义动机,比如 “我欲仁,斯
仁至矣”(《论语·述而》)。在政治建构上,基于自我道德动机建立且不追求实力、而寻
求 “来者悦”的政治体,以均富和安适让人心悦诚服。“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述而》)而在中国古代实际政治运行中,以五服制
度、天下体系建构的中国古代 “国际”政治逻辑,通过文野设定来建构世界秩序,被卷
入天下体系的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国的蛮性国家。因此,中国是他们的文明提升
者、利益输出者、危难拯救者。至于被纳入天下体系的其他古代国家做何反应,不是这一
体系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赵汀阳认为,中国的天下体系是一个 “漩涡模式”,中国按
照自己的运作模式旋转,别国是主动卷进来的,中国并没有征服这些国家,但中国却以和
平方式处于不停的扩展状态。这样的断定,自然是中国自身基于自我高尚动机的 “夫子
①
① 赵汀阳设问,“中国是什么?中国从不侵略和扩张,但为什么越来越扩大?”他的回答是 “一个漩涡模型,正好
能够解释中国为什么不是扩张的,但是能够变大:漩涡不是对外的,不是离心的,它的力量是向心的,把周边
的各种地区包围进来,不断往中间卷,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越吸东西越多,漩涡中心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且
是停不下来的。”赵汀阳:“中国古代的漩涡生长模式”,http:/ / cul. sohu. com/ s2016 / zhaotingyang/ 访问时间:
2019年 12月 31日。
6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