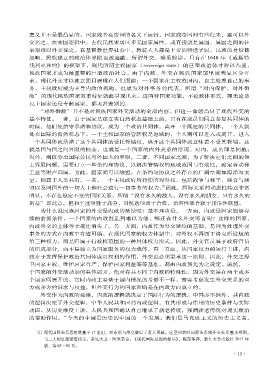Page 12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P. 12
意义并不是最凸显的。国家或者在帝国的名义下运行,国家或帝国间有些往来,差可以外
交名之。在帝国逻辑中,古代民族聚居区多无国家属性,或直接就是属国,属国之间的往
来很难以外交视之。在基督教世界社会中,教徒人人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民族的身份被
忽略,民族建立的政治体界限也被遮蔽。所谓外交,难觅踪影。只有在 1648 年 《威斯特
伐利亚和约》的框架下,现代所谓主权国家 ( sovereign state)的巨型政治体才得以凸显,
民族国家才成为最重要的巨型政治社会。由于内政、外交在民族国家那里被明显区分开
来,现代外交才以独立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国家在主权范围内,自主处理自己的事
务,主权政府成为主导内政的机构,也成为对外事务的代表。所谓 “对内保护,对外御
敌”的现代民族国家双重特征就此呈现出来。这两种国家功能,不论政体形式,即无论是
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无甚差别的。
“对外御敌”并不是对民族国家外交活动的全部内容。但这一命题凸显了现代外交的
基本特征。一者,由于国家是建立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只有在成员们同意参加共同体的
时候,他们便信守承诺和协议,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离开一个既定的共同体,一个人就
处在国际的自然状态下。一个主权国家的管辖权是地域的,个人则可以进入或离开。进入
一个共同体就承诺了这个共同体的受托管辖权,离开这个共同体就意味着不受其管辖。这
就是国与国之间界限的标志,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内外关系的浮现。对内,成员即是同胞;
对外,则区分出国际公民与外国人的界限。二者,不同国家之间,为了解决它们之间的领
土界限问题,需要订立一些条约和协议,以解决管辖权的地域范围与有效性,确定劳动和
工业等财产归属。为此,国家间可以结盟。在条约与协议之外存在的广阔空间如海洋与太
空,则属于人类共有。三者,一个主权政府所行使的对外权,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
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因此,国际关系的动态性特点非常
①
明显,不存在稳定不变的国际关系。所谓 “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
利益”即此意。但和平选项胜于战争,对抗选项弱于合作,兼容性联合强于排斥性联盟。
为什么说民族国家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呢?基本理由是,一方面,内政是国家能够存
续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内政混乱到难以为继,哪还有什么外交可言呢?这样的国家,
内政外交的主体等于接连消失了。另一方面,内政作为外交延续的基础,是因为处理外交
事务的方式在内政中有迹可循。在现代国家的权力体制中,对外权不再属于洛克所设想的
第三种权力,而是归属于行政权范围的一种具体权力形式。因此,外交官员属于政府官员
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为国家服务的权力载体。再一方面,从国家权力的运行上讲,内
政在于发挥保护政治共同体成员权利的作用,外交也必须秉承这一原则。因此,外交之捍
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尊严、保护国家利益等等基准,都由内政预先为之设定。诚然,一
个国家的外交活动如何具体展开,绝对有其不同于内政的特殊性。因为外交是在两个或多
个国家间展开的,它同内政主要基于国内情况的考量不一样,需要考虑发生外交关系的双
方或多方的诉求与权益。但外交行为的国家准则是在内政方面奠立的。
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内政的逻辑就决定了国际行为的逻辑。中国亦不例外,其内政
的逻辑决定了外交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逻辑,有其形成与作用的历史条件与实际
动因。从历史维度上讲,人民共和国确认自己继承了新老传统,强调新老传统对现实政治
的帮助作用。“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① 现代国际关系思想奠基于 17世纪,霍布斯与洛克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里列举的国际关系或外交关系基本准则,
与二人的思想紧密相关。参见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陈茂华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版,第 63 - 94页。
1 ·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