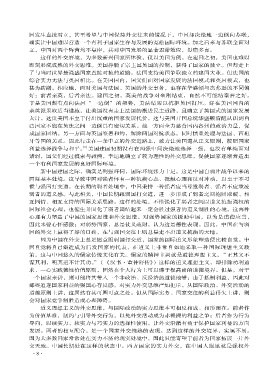Page 9 - 《党政研究》2020年第2期
P. 9
国发生直接对立,甚至希望与中国保持外交往来的情况下,中国却决绝地一边倒向苏联,
确实让中国难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宽松国际环境。加之后来与苏联全面对
立,中国对两个阵营均不靠岸,其对中国发展的显著迟滞效应,毋庸多言。
这样的外交窘境,为多数新兴国家所体验,仅以美国为例。在建国之初,美国也难以
即刻形成成熟的外交思维。美国挣脱了宗主国英国的控制,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但却走上
了与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直接对抗的道路。法国支持美国争取独立的建国大业。但法国的
综合实力无法与英国相比。在美国国内,国父们面对国家发展的法国模式和英国模式,也
甚为踌躇。相应地,面对美国与法国、英国的外交事务,也存在华盛顿与杰弗逊的不同偏
好:前者亲英,后者亲法。建国之初,英美的战争对垒刚结束,自然不可能结秦晋之好。
于是美国颇有点向法国 “一边倒”的架势,美法结盟以抗拒英国打压。好在美国国内的
亲英派采取适当措施,让美国没有走上法国的激进民主道路,且确立了英国式的国家发展
大计。这让美国不至于付出沉重的国家发展代价。这与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清醒认识到自
己国家不能在英法之间一边倒具有密切关系。他一方面全力整合国内各州的政治力量,促
成国家团结。另一方面与英国签署和约,解除两国对抗状态。同时慎重处理与法国、西班
牙等国的关系。因此行走在一条中立的外交进路上,致力让美国遵从正义原则,按照国家
利益选择战争与和平。 美国建国初期没有在两强中间决绝地选择一强,也没有单纯面对
〔 6〕
诸弱,国父们经过摸索与碰撞,幸运地确立了较为理性的外交思维,促使国家逐渐营造出
一个有利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新中国建国之际,确实是列强环伺,国际环境张力十足。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
国际基本处境。这导致中国对强者怀有一种抗衡心态、抵触心理和反对冲动,以至于不习
惯与强国打交道。在长期的弱者处境中,中国秉持一种强者应当尊重弱者、强者不应欺凌
弱者的道义感。与此相关,中国长期跟弱国打交道,进一步形成了弱者之间抱团取暖、相
互同情、相互支持的国际关系思路。这样的处境,不惟强化了弱者之间以道义抗拒强权的
国际社会心理,也催生并固化了弱者团结起来一定会胜过强者的道义制胜的心境。这两种
心理有力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思维和外交思维。对强势国家的援助中国,以为是道德应当,
因此未曾心怀感激;对弱势国家,总是仗义疏财,认为这是德性表现。因此,中国在与弱
国的外交上赢得了好的口碑,在与强国交往上则总是走不出道义抗衡的天地。
因为中国在外交上总是愿意跟弱国打交道,国家的国际道义形象塑造便比较自觉。中
国自觉将自己塑造成为后发国家的代表,在道义上非常自如地采取一种国际理想主义政
策。这与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文化有关。儒家的精神主调就是道德理想主义。“正其义不
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这样的道义理想主义,即排除功利追
求、一心实践德性价值原则,固然在个人行为上可以臻于极高尚的道德境界。但是,对于
一个国家来讲,则可能将其带入一个非政治、反经济的道德地带:由于抵制利益,因此对
那些追逐国家利益的强国心存反感,对实力外交思维严加拒斥。从国际政治、外交活动的
道德原则上讲,这固然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但从国际实务、国家交往的利益得失上讲,则
会对国家竞争制胜造成心理障碍。
道义理想主义的外交思维,与国际政治的实力思维本可相反相成、相形而在。前者作
为价值基准,制约与引导外交行为,以免外交活动成为赤裸裸的利益之争;后者作为行为
导向,以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选择性使用,让外交沿循有益于保护国家利益的方向
发展。两者的相互配合,是一个国家外交纯熟的表现。达到这样的外交境界,实属不易。
因为大多数国家常常处在实力不济的现实处境中,因此只能寄望于前者为国家拓展一片外
交天地。中国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西方国家的实力外交,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强权外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