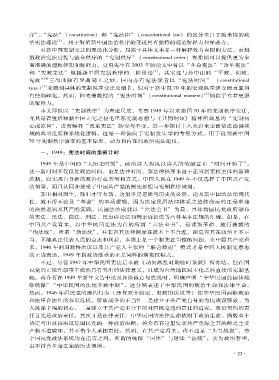Page 23 - 党政研究2019年第5期
P. 23
序”。“宪法”( constitution)和 “宪法律”( constitutional law)的区分来自于施米特的政
治宪法理论 ,用于解析新中国法治秩序的变迁具有独特的理论解释力和穿透力。
〔 2〕
对新中国宪制变迁的理论化分析,局限于具体文本是一种解释效力有限的方法,而侧
重政治宪法过程与整全秩序的 “宪制秩序”( constitutional order)视角则可以提供更为全
面准确的理解框架和解释力。夏勇先生在 2003 年的论文中曾以 “革命宪法”“改革宪法”
和 “宪政宪法”概括新中国宪制秩序的三阶段论 ,其实这与孙中山的 “军政、训政、
〔 3〕
〔 4〕
宪政” 三部曲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国内亦有宪法学者以 “宪法时间” ( constitutional
time) 来雕刻具体的宪制秩序变迁及细节,但对于新中国 70 年的宏观秩序演变而言显得
〔 5〕
有些细碎化。然而,阿克曼教授的 “宪法时刻”( constitutional moment) 则似乎有着更强
〔 6〕
的解释力。
本文即拟以 “宪制秩序”为理论尺度,考察 1949 年以来建国 70 年的宪制秩序变迁,
尤其是着重解释新中国立宪之初毛泽东宪制思想与 《共同纲领》精神所奠基的 “宪制初
心或原旨”,进而解释 “改革宪法”的变与不变,进一步探讨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领
域的典型进展和系统化逻辑。这是一种偏向于宪制发生学的考察方式,用于说明新中国
70 年宪制秩序演变的基本原理、动力和内在的政治宪法逻辑。
一、1949:宪法时间的重新计时
1949 年是中国的 “大历史时刻”,政治诗人胡风以诗人的笔触宣布 “时间开始了”。
这一新时间不仅仅是政治时间,也是法律时间。新法律秩序来自于正当制宪权主体的新颖
决断,以实现自身新的政治存在类型和方式。中国人民在 1949 年不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而且认同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宪思想与宪制秩序规划。
新旧相对而生,除旧才可布新,这似乎是逻辑与历史的必然。论及新中国的法治现代
性,就不得不论及 “革命”的本质逻辑,因为决定民国法律体系之整体命运的正是革命
的决然逻辑及其严酷实践。民国法治成就以 “六法全书”为最,具体指国民党政府颁布
的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六种基本法规的汇编。但是,在
中国共产党看来,以中华民国宪法为首的所谓 “六法全书”,是背叛革命、施行独裁的
“伪法统”。所谓 “伪法统”,并非言其法律制度在技术上不合理,而是言其在政治上不正
当,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本质上是一个制宪正当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看
来,1946 年的旧政协决议以及共产党人主张的 “联合政府”模式才是中国人民制宪意志
的正当表达,1949 年新政协继承的正是同样的制宪权模式。
不过,尽管 1947 年中华民国宪法后来被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冻结,但在国
民党的正统性叙事中依然具有突出的法律意义,且成为台湾地区民主化之后直接的宪制基
础。蒋介石在 1949 年新年文告中论及和谈诚意与底线时,明确声明 “中华民国的国体能
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这分别表述了中华民国的政治生命和法律生命。
然而,1946 年国民党的违约行为 (违背双十协定、旧政协决议等)使中华民国面临政治
和法律合法性的双重危机。解放战争的正当性一是建立于共产党自身的为民族谋解放、为
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二是建立于共产党主导下的对国民党违约责任的追究。政治契约的责
任首先是政治责任,其次才是法律责任。中华民国的法律生命依附于政治生命。撕毁双十
协定与旧政协决议是国民党的一种政治决断,蒋介石在这里要求共产党保全其决断之主要
产物不遭破坏,并不惜个人承担责任。然而,在共产党看来,蒋不过是 “头号战犯”,整
个国民党政法系统均在追责之列。所谓的确保 “国体”与延续 “法统”,实为政治奢望,
也不符合革命立宪的历史惯例。
3 ·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