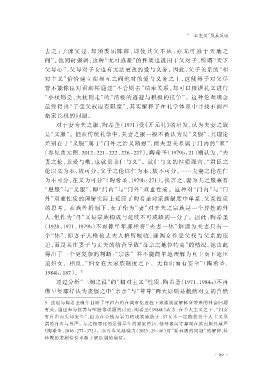Page 96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96
“一本主义”及其反思
去 之 ; 子 谏 父 过 , 却 须 委 屈 陈 辞 , 即 使 其 父 不 从 , 亦 无 可 逃 于 天 地 之
间”。 他同时强调,这种“无可逃避”的性质也适用于父对子,所谓“天下
父母心”,父母对子女也有无法更改的爱与义务。 因此,父子关系的“相
对主义”恰恰建立在相互之间绝对的爱与义务之上,这使得子对父尽
管不能像臣对君那样通过“不合则去”结束关系,却可以根据礼义进行
“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消极的逃避与积极的抗争”。 这种伦理观念
最终得出“子受父权应有限度”,其实解释了在礼学体系中寻找不到严
格家长权的问题。
对于妻为夫之服,陶希圣( 1971)受《开元礼》的启发,认为夫妻之服
是“义服”。 但在传统礼学中,夫妻之服一般不被认为是“义服”,其理论
差别在于“义服”属于“门外之治义断恩”,而夫妻关系属于门内的“家”
(参见曹元弼,2012:221-222、226-227)。 陶希圣(1979b:21)则认为,“夫
妻之伦,兼爱与敬,也就是兼仁与义”。 就仁与义的性质而言,“君臣之
伦以义为本,故可分。父子之伦以仁为本,故不可分。……夫妻之伦在仁
为不可分,在义为可分”(陶希圣,1979b:271)。 换言之,妻为夫之服兼有
“ 恩服”与“义服”,即“门内”与“门外”双重性质。 这种对“门内”与“门
外”双重性质的理解实际上延续了陶希圣对家族制度中单系、父系性质
的思考。 在族外婚制下,女子作为“妻”对于夫之宗族是一个异姓的外
人,但作为“母”又是宗族构成与延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因此,陶希圣
(1928,1971,1979b)不再像早年那样将“夫妻一体”解读为夫妻只有一
个“体”,即妻子人格被丈夫人格所吸收,强调女性受父权与父系的压
迫,而是关注妻子与丈夫的结合导致“母亲之地位特高”的情况。他由此
得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判断:“宗法” 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自上而下地压
迫妇女, 相反,“妇女在大家族制度之下, 无自由而有安全”(陶希圣,
1984b:187)。 5
通过分析“三纲之说”的“相对主义”性质,陶希圣(1971,1984a)不再
像早年那样认为丧服之中“亲亲”与“尊尊”两大原则是截然对立的自然
5. 这也与陶希圣晚年目睹了中国台湾在城市化进程下家族制度解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有关。 通过参与抚养与堕胎等议题的讨论,陶希圣( 1984b)认为,在个人主义之下,“妇女
有自由而失却安全”,因为在金钱与暴力的现实威胁下,妇女不一定能获得个人主义承
诺的自由与尊严。 与之相对比的是他早年的家庭经历,他母亲虽守寡而在族内颇具威严
(陶希圣,2016:277-372)。 亦可参见赵晓力(2023:29-46)对“祥林嫂的问题”的解释,祥
林嫂的悲剧恰恰来源于宗法制的崩溃。
·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