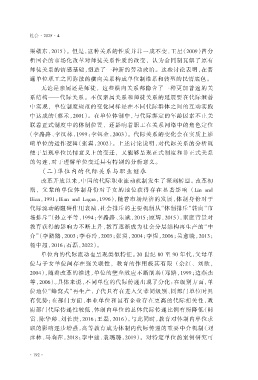Page 199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199
社会·2025·4
渠敬东,2015)。 但是,这种关系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王星(2009)曾分
析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对师徒关系性质的改变, 认为合同制瓦解了原有
师徒关系的情感基础,塑造了一种新的劳动政治。 这些讨论表明,在普
通单位职工之间弥散的横向关系构成单位制维系和转型的民情底色。
无论是亲属还是师徒, 这些横向关系都隐含了一种更加普遍的关
系结构——代际关系。 不仅亲属关系和师徒关系的延展要在代际继替
—
中实现, 单位制度规范的变化同样是在不同代际群体之间的互动实践
中达成的(蔡禾,2001)。 在单位体制中,与代际绑定的年龄因素不止关
联着正式制度中的体制位置, 还影响着职工在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定位
(李路路、李汉林,1999;李铒金,2003)。 代际关系的变化会在实质上影
响单位的运作逻辑(张翼,2002)。 上述讨论说明,对代际关系的分析既
便于呈现单位民情意义上的变迁, 又能够呈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关系
的勾连,对于理解单位变迁具有特别的分析意义。
(二)单位内的代际关系与职业继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代际职业流动机制发生了深刻转型。 改革初
期, 父辈的单位体制身份对子女的地位获得 存 在 显 著 影 响 ( Lin and
Bian,1991;Bian and Logan,1996),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身份对于
代际流动的阻碍作用衰减,社会排斥的主要机制从“体制排斥”转向“市
场排斥”(孙立平等,1994;李路路、朱斌,2015;顾辉,2015),家庭背景对
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教育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结构再生产的“中
介”(李路路,2003;李春玲,2003;张翼,2004;李煜,2006;吴愈晓,2013;
杨中超,2016;石磊,2022)。
单位内的代际流动也呈现类似特征。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父母单
位与子女单位间存在强关联性, 教育的作用极其有限 (余红、 刘欣,
2004),随着改革的推进,单位的壁垒效应不断削弱(郑路,1999;边燕杰
等,2006)。具体来说,不同单位的代际传递出现了分化:在级别方面,单
位地位“ 蜂窝式”再生产,子代只有在进入父辈同级别、同部门单位时具
有优势;在部门方面,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存在更高的代际相关性,政
府部门代际传递性较低,体制内单位的总体代际传递比例有所降低(韩
雷、陈华帅、刘长庚,2016;王磊,2016)。 与此同时,教育对体制内单位求
职的影响逐步增强,高等教育成为体制内代际传递的重要中介机制(刘
彦林、马莉萍,2018;李中建、袁璐璐,2019)。 对特定单位的案例研究可
·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