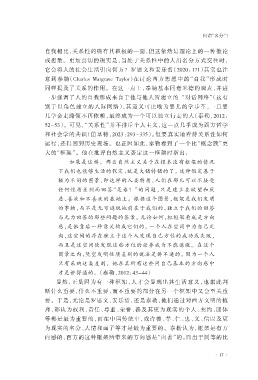Page 24 - 《社会》2024年第6期
P. 24
何谓“名分”?
自我相比,关系性的确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这依然是理论上的一种推论
或想象。 更加真切的现实是,当处于关系性中的人用名分方式交往时,
它会将人的社会生活引向何方? 罗思文和安乐哲(2020:171)其实也注
意到泰勒( Charles Margrave Taylor)在讨论西方思想中的“自我”形成时
同样提及了关系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泰勒基本同意米德的观点,并进
一步强调了人的自我形成来自于他与他人所建立的“对话网络”(这有
别于以角色建立的人际网络),其意义可比喻为婴儿的学步车,一旦婴
儿学会走路便不再依赖,最终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行走的人(泰勒,2012:
52-53)。 可见,“关系性”并不排斥个人主义,这一点几乎成为西方哲学
和社会学的共识(伯基特,2023:293-335)。 但要真实地看待关系性如何
运行,还得回到历史现场。 也正因如此,泰勒看到了一个比“概念簇”更
大的“框架”。 他在批评自然主义否定这一框架时指出:
如果是这样, 那么自然主义关于在根本没有框架的情况
下我们也能够生活的假定,就是大错特错的了。 这种假定基于
极为不同的图景,即这样的人类特质,人们在那儿可以不接受
任何性质差别而回答“是谁? ”的问题,只是建立在欲望和厌
恶、喜欢和不喜欢的基础上。 根据这个图景,框架是我们发明
的事物,而不是无可逃脱地前在于我们的、独立于我们的回答
与无力回答的那些问题的答案。 无论如何,把框架看成是方向
感,是依靠后一种意义构成它们的。 一个人在空间中为自己定
向,这空间的存在独立于这个人发现自己方位的成功或失败,
而且是这空间使发现这些方位的任务成为不能逃避。 在这个
图景之内,凭空发明性质差别的说法是讲不通的。 因为一个人
只有采纳这类差别, 他在其所有这些问自己基本的方向感中
才是讲得通的。 (泰勒,2012:43-44)
显然,正是因为有一种框架,人才会显现出其生活意义,也据此判
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而不重要的部分在另一个框架中又会至关重
要。 于是,无论是罗思文、安乐哲,还是泰勒,他们通过对西方文明的梳
理,都认为权利、责任、尊重、荣誉、善及其更为现实的个人、契约、团体
等都是最为重要的,而在中国传统中,或许善、孝、仁、忠、义、信以及更
为现实的名分、人情和面子等才是最为重要的。 泰勒认为,框架是有方
向感的,西方的这种框架所带来的方向感是“向善”的。而出于同等的比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