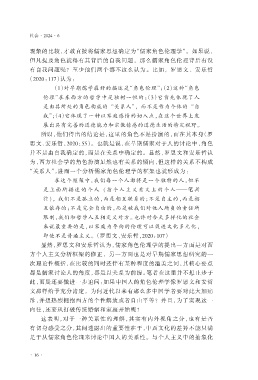Page 23 - 《社会》2024年第6期
P. 23
社会·2024·6
现象的比较,才敢直接将儒家思想确定为“儒家角色伦理学”。 如果说,
但凡提及角色就得有其背后的自我问题, 那么儒家角色伦理背后有没
有自我问题呢? 至少他们两个都不这么认为。 比如, 罗思文、 安乐哲
( 2020:117)认为:
(1)对早期儒学最好的描述是“角色伦理”;(2)这种“角色
伦理”在东西方的哲学中是独树一帜的;(3)它首先体现了人
是由其所处的角色构成的“关系人”, 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自
我”;(4)它体现了一种以家庭感情的切入点,在这个世界上发
展出具有完善的道德能力和宗教情感的道德生活的特定视野。
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角色不是扮演的,而在其本身(罗
思文、安乐哲,2020:55)。 也就是说,在早期儒家对于人的讨论中,角色
并不是由自我确定的,而是在关系中确定的。 显然,罗思文和安乐哲认
为,西方社会学的角色扮演虽然也有关系的倾向,但这样的关系不构成
“关系人”,进而一个分析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框架也就形成为:
在这个框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是一个独特的人,但不
是上面所描述 的 个人 ( 指 个 人 主 义 意 义 上 的 个 人 ———笔 者
注 )。 我们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是自主的,而是相
互依存的;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被我们对他人所负的责任所
限制,我们和哲学人互相定义对方。 也许对今天多样化的社会
来说最重要的是,以家庭为导向的伦理可以促进文化多元化,
即使不是普遍主义。 (罗思文、安乐哲,2020:107)
显然,罗思文和安乐哲认为,儒家角色伦理学的提出一方面是对西
方个人主义分析框架的修正, 另一方面也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一
次理论性概括,在比较的同时还伴有某种程度的溢美之词,其核心要点
都是儒家讨论人的角度,都是以关系为前提。 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止步于
此,而是还要做进一步追问:如果中国人的角色伦理学像罗思文和安哲
文那样给予充分肯定, 为何近代以来有那么多中国学者要对此大加痛
斥,并想热烈拥抱西方的个性解放或者自由平等? 并且,为了实现这一
向往,还要从打破传统婚姻和家庭开始呢?
这表明,对于一种关系性的理解,其实有内外视角之分,也有是否
有切身感受之分,其间透露出的重要性在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不能只满
足于从儒家角色伦理来讨论中国人的关系性。 与个人主义中的抽象化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