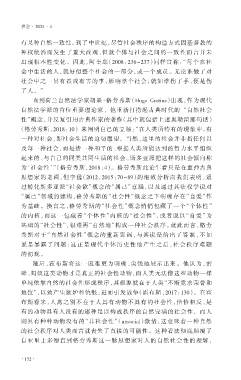Page 159 - 《社会》2024年第4期
P. 159
社会·2024·4
有某种自然一致性。 到了中世纪,尽管社会秩序的构造方式因基督教的
神权统治而发生了重大改观,但就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致性而言并未
出现根本性变化。 因此,阿奎那(2008:236-237)同样宣称:“每个在社
会中生活的人,就好似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或一个成员。 无论谁做了对
社会中之一员有益或有害的事,影响整个社会;就如谁伤了手,便是伤
了人。 ”
直到荷兰自然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出现,作为现代
自然法学派的首位重要理论家, 他重新打捞起古典时代的“自然社会
性”概念,并反复引用古典作家的著作(其中就包括上述奥勒留那句话)
(格劳秀斯,2018:10) 来阐明自己的立场:“在人类所特有的现象中,有
一种对社会,即社会生活的迫切愿望。 当然,这里的社会并非指任何以
及每一种社会,而是指一种和平的、根据人类所能达到的智力水平组织
起来的、与自己的同类共同生活的社会。 斯多亚派把这样的社会倾向称
为‘社会性’”(格劳秀斯,2018:4)。 格劳秀斯此论乍看只是在重弹古典
思想家的老调,但李猛(2012,2015:70-89)的细致分析向我们表明,通
过转化斯多亚派“社会欲”概念的“属己”意涵,以及通过其法权学说对
“属己”领域的建构,格劳秀斯的“社会性”概念之下明确存在“自爱”作
为基础。 换言之,格劳秀斯的“社会性”概念悄悄包藏了一个“个体性”
的内核,而这一包藏着“个体性”内核的“社会性”,或者说以“自爱”为
基础的“社会性”,很难再“自然地”构成一种社会秩序。 就此而言,格劳
秀斯对于“自然社会性”概念的重新强调,与其说是给出了答案,不如
说是暴露了问题:这正是现代个体历史性地产生之后,社会秩序难题
的初现。
随后,霍布斯将这一困难更为明确、尖锐地展示出来。 他认为,蜜
蜂、蚂蚁这类动物才是真正的社会性动物,而人类无法像这些动物一样
单纯依靠自然的社会性形成秩序,其根源就在于人类“不断竞求荣誉和
地位”,以致产生嫉妒和仇恨,进而引发战争(霍布斯,2017:130)。 在霍
布斯看来,人禽之别不在于人具有动物不具有的社会性,恰恰相反,是
有的动物具有人没有的那种足以构成秩序的自然完满的社会性, 而人
则具有种种动物没有的“非社会性”(unsocial)激情,这意味着一种自然
的社会秩序对人类而言就丧失了直接的可能性。 这种看法彻底颠覆了
自亚里士多德直到格劳秀斯这一脉思想家对人的自然社会性的理解,
·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