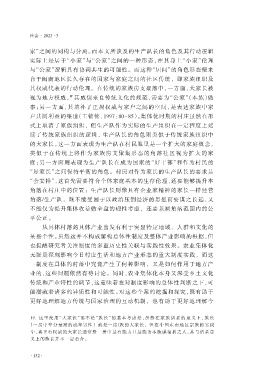Page 139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139
社会·2023·3
家”之间的同构与分离。 而本文所谈及的生产队长的角色及其行动逻辑
实际上是居于“小家”与“公家”之间的一种形态,在其身上“小家”伦理
与“公家”逻辑具有协调共生的可能性。 而这种“居间”的角色形态便来
自于闽南地区长久存在的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社区传统, 即家族组织及
其权威代表的行动伦理。 在传统的家族房支聚落中,一方面,大家长被
19
视为地方权威, 其威信来自传统文化的规范,需要为“公家”(本族)做
事;另一方面,其填补了正规权威与家户之间的空间,是表达家族中家
户共同利益的渠道(王铭铭,1997:80-85)。集体化时期的村庄虽然在形
式上取消了家族组织, 但生产队作为实际的生产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延
续了传统家族组织的逻辑, 生产队长的角色则类似于传统家族组织中
的大家长。 这一方面表现为生产队在村民眼里是一个扩大的家庭概念,
类似于在传统上将作为家族房支聚集形态的角落 社区视 为扩 大的家
庭;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生产队长在成为国家的“好干部”和作为村民的
“好家长”之间保持平衡的角色。 村民对作为家长的生产队长的要求是
“会安排”,这首先需要符合个体家庭基本的生存伦理,还要能够提升本
角落在村庄中的位置; 生产队长则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家长一样经营
角落/生产队, 既不能受困于以政治压倒经济的思想而要谋之长远,又
不能仅为提升集体收益做全盘的理性考虑, 还要兼顾角落范围内的公
平公正。
从具体村落的具体产业出发有利于突显特定地域、 人群和文化的
某些个性。 虽然这并不构成解构总体性制度及整体产业影响的根据,但
也提醒研究者关注制度的多重历史性关联与实践性效果。 农业集体化
无疑是深刻影响今日村庄生活和地方产业形态的重大制度实践, 而这
一制度在具体的村落中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又是如何作用于地方产
业的,这些问题依然有待讨论。 同时,农业集体化本身又深受乡土文化
传统和产业特性的调节,这意味着在对制度影响的总体性判断之下,可
能潜藏着诸多的异质性和可能性。 对这些个案的挖掘和探究,既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地方传统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机制, 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今
19. 这里使用“大家长 ”而不是“族长”的 基本考 虑是,虽 然在 家 族 谱 系 的 意 义 上 , 族 长
(一房中辈分最高的成年男性) 就是一房/族的大家长, 但在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的实践
中,真正有权威的大家长通常是一房中最有能力且最能为本族谋福利之人,其与谱系意
义上的族长并不一定重合。
·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