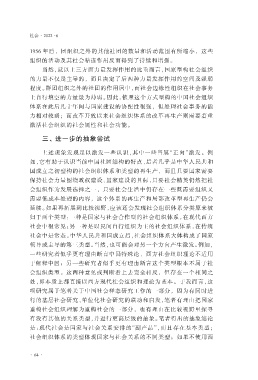Page 71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71
社会·2022·6
1956 年后, 团组织之外的其他社团的数量和活动范围有所缩小, 这些
组织的活动及其社会粘连作用反而得到了持续和增强。
当然,就以上三方面力量发挥作用的比重而言,国家型构社会组织
的力量不仅是主导的, 而且决定了后两种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及强弱
程度。 群团组织之外的社团的作用居中,而社会边缘性组织在社会事务
上自行填空的力量最为薄弱。 因此,依照这个方式型构的中国社会组织
体系在此后几十年间与国家建设的协配性很强, 但处理社会事务的能
力相对较弱; 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体系的改革再生产则需要着重
激活社会组织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
三、 进一步的抽象尝试
上述现象发现足以激发一些认识,其中一些当属“正向”激发。 例
如,它有助于认识当前中国社团结构的特点,后者几乎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型构的社会组织体系和类型的再生产, 而且只要国家需要
保持社会力量围绕政权建设、国家建设的目标,只要社会精英仍然把社
会组织作为发展选择之一, 只要社会生活中仍存在一些既需要组织又
需要低成本处理的内容, 这个体系的再生产和局部改革型再生产仍会
延续。 如果再拓展到比较视野,应该还会发现社会组织体系分类原来被
归于两个类型:一种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型的社会组织体系,在现代西方
社会中很常见;另一种是以民间自行组织为主的社会组织体系,在传统
社会中是常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组织体系大体构成了国家
领导或主导的第三类型。当然,也可能会对另一个方向产生激发。例如,
一些研究者似乎更有理由断言中国特殊论, 西方社会组织理论不适用
于解释中国; 另一些研究者似乎更有理由断言这个类型根本不属于社
会组织类型。 这两种意见或判断看上去完全相反, 但存在一个相同之
处,即本质上都直接以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和理论为蓝本。 于我而言,这
项研究属于笔者关于中国社会样态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因为有同时进
行的基层社会研究、单位化社会研究的联动和启发,笔者有理由把国家
重构社会组织理解为重构社会的一部分, 也有理由在比较视野里探寻
有没有其他的关系类型,并进行更高层级的抽象。 笔者得出的抽象结论
是:现代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安排的“副产品”,而且存在基本类型;
社会组织体系的类型体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 如果不使用西
· 64 ·